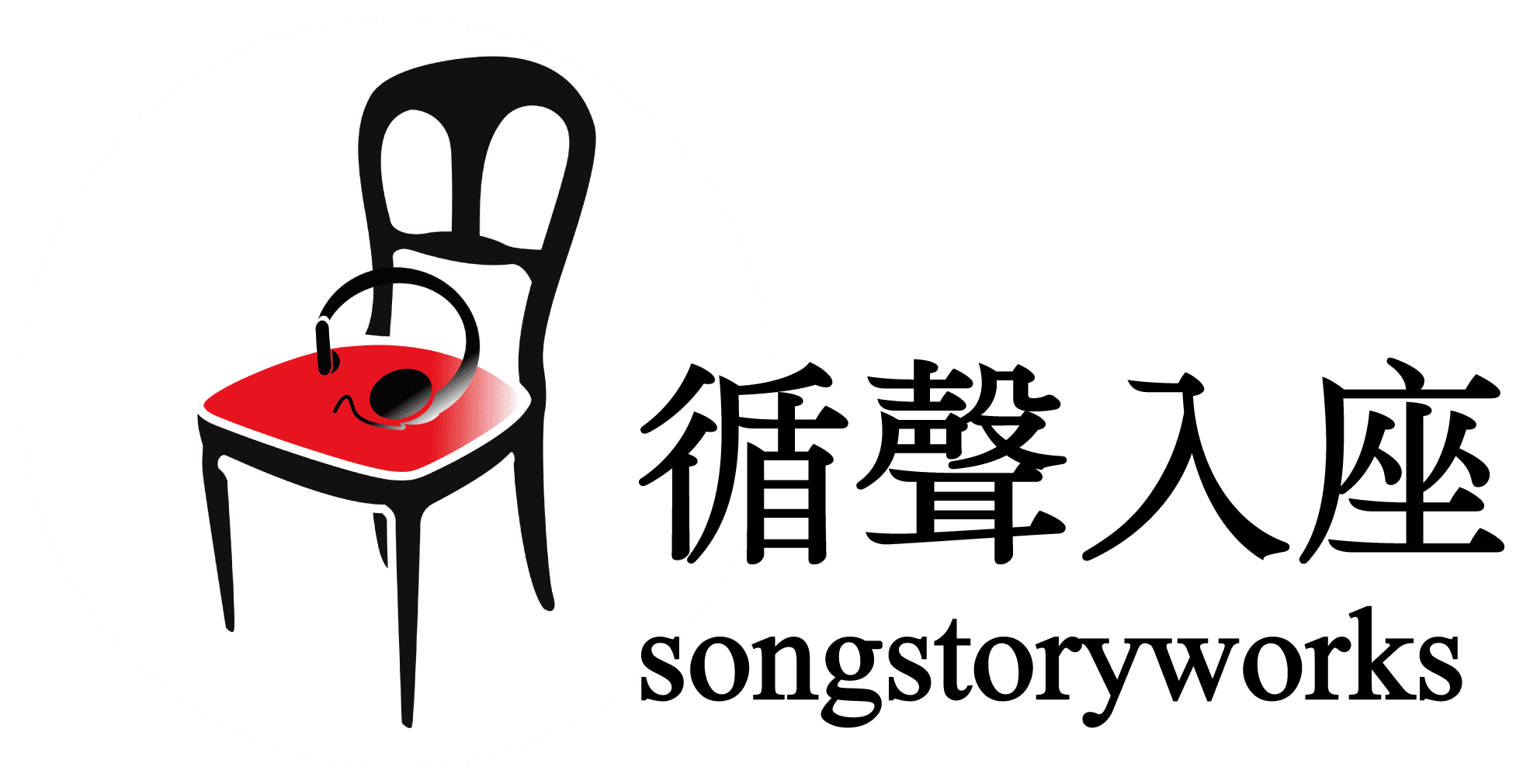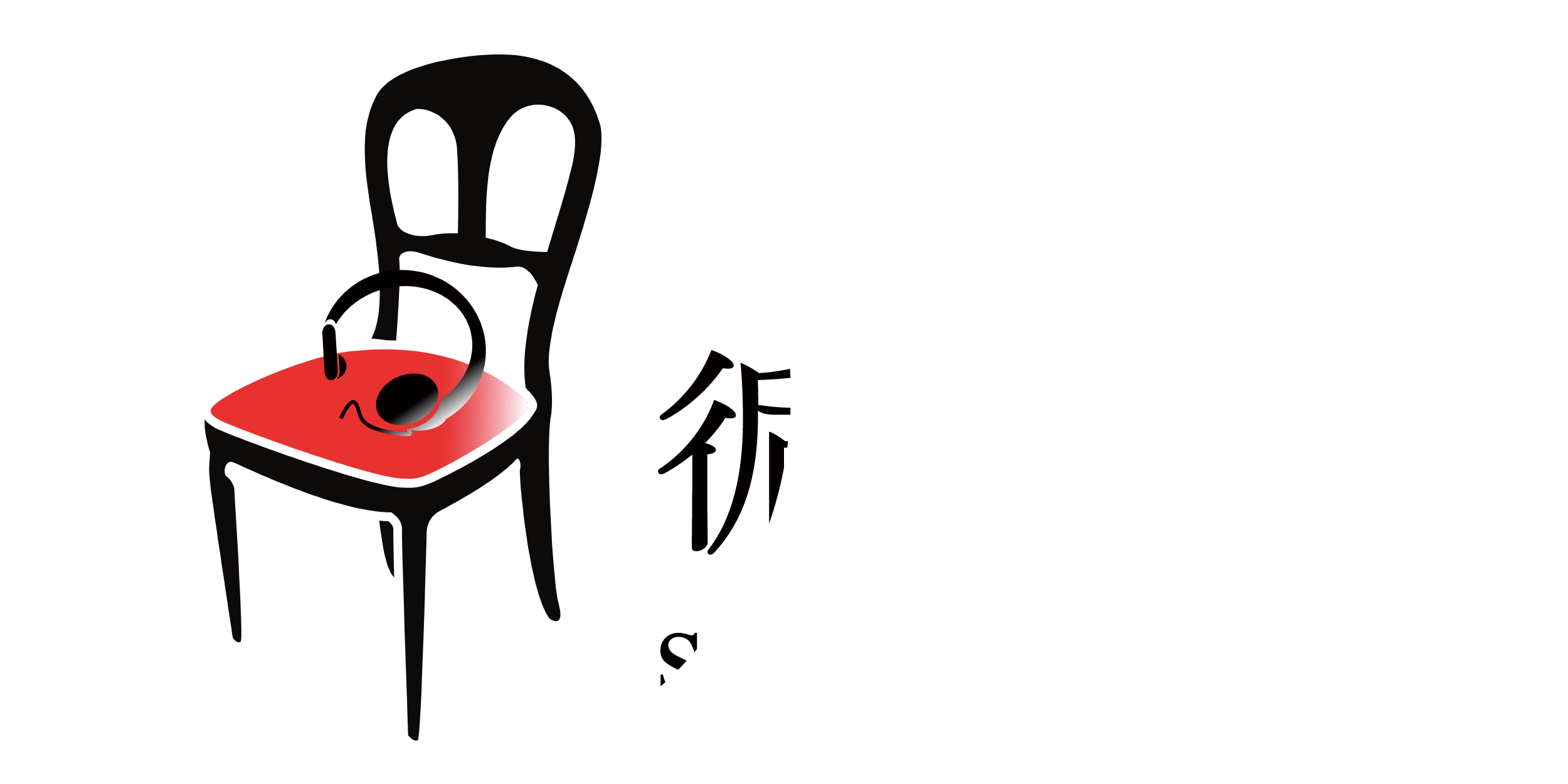時間,發專輯前一個多月,地點,羅晧宇家,家裡有隻狗狗Buffet。團員四人坐在客廳配著時不時發出的汪汪叫聲,在有限的時間裡,暫時拋下了待會的演講、快喘不過氣的專輯收尾壓力,談著創作過程的故事。就像我們正在許多日常的小挑戰中談論那些Little Battle,生活就是如此地後設,帶點荒謬、無奈卻只能苦中作樂。
採訪過程中,吉他手阿雷突然分享了在書中看到的一句話,說:「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人,他都有自己要面對的戰爭。」那是他為這張專輯名《 Little Battle 》給出的感想。阿雷進一步解釋,「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有難關要面對,那是不是可以多對其他人好一些?」
挑戰、抉擇、失去、遺憾,從站定樂團說故事調性的首專《末日倒數的庸俗週記》,經過在艱苦中拾得的首張EP《得意的一天》到成團邁入第五年,準備替樂團尋得定位的二專《 Little Battle 》,他們用許多戲劇化同時也不可抗力的真實故事,堆疊出作品厚度,這次更透過同步錄音保留樂團演出的真實臨場感,與製作人韓立康巧手共搭出一張聽感和創作內容皆臻成熟的作品。
正在「成長痛」的樂團
要說第一張專輯到第二張有什麼蛻變的話,說來簡單就是彼此更熟悉了。貝斯手晧宇說,Little Battle這詞正好可以做為這段時間的體悟,「日常當中都會遇到很多挑戰,這些挑戰過後你就自然地長大了。」從2020年尾與三十萬年老虎鉗前團員阿雷,找來主唱家耘、鼓手允祈共組「庸俗救星」,玩團這幾年除了彼此熟悉,某部分也越來越相像。這樣的默契之於創作一環,已漸漸成為日常一隅。
「但要說團員間和第一張(專輯)有什麼蛻變的話,覺得是我們三人的寫歌數量變得更平均了。」晧宇說的三人,包含他,還有阿雷和家耘。過去第一張專輯帶進來的作品多是庸俗救星還未成團前,阿雷先寫出來的歌。當時家耘需要問他們怎麼唱才能達到他們心中的畫面,而少數幾首家耘的創作也需要透過摸索才能做出適切的編曲,「現在數量平衡了,我們的創作也開始各自變得不一樣,我覺得挺好的。」
專輯同名曲便是由家耘主筆,以「little girl」為視角,短短兩分鐘充分展現自內斂到昂揚的過程,成長如同此般,在反覆中漸漸生出不同的樣貌。
這些年他們把樂團定位為「樂觀的悲劇演員」,看似衝突,但用音樂來表達卻容易許多,家耘說他們特別想用相較浪漫的方式,來表現生命中碰到強烈或衝擊的事情。而Little Battle對她來說不只是小事、不重要的事,還包含了相對沉重的生活變故,但似乎用著詼諧的口吻,就能好好地對抗那些「成長痛」。具體有哪些?採訪當下正值他們專輯收尾階段,仍在為時間緊迫而感到焦慮,談起〈生活失竊記〉時,晧宇大喊:「我其實已經忘記當時我在錄什麼了!太趕了啦!」
換來的是什麼?
填滿無底慾望的自由
賺來的為什麼?
彌補剩下一半的缺口
這首來自阿雷的詞曲創作,也是團員公認最能代表現階段樂迷對庸俗救星想像的搖滾作品。開場合成器音效彷彿帶領聽者暫時抽離枯燥的現實,講述人生被工作切割,只剩不到一半時間是自己的。「這首歌是我在做上張EP時,有段時間去上班的心得。我也參考了自己很喜歡的影集叫《人生切割術》,算是有感而發。」阿雷分享道。而歌曲末尾約一分鐘的段落相當精采,弦樂與合成器交錯前行,吉他riff像是致敬阿雷在首張專輯中寫的〈窗簾〉,偷偷帶起了陪伴一詞,在看似混亂失去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絲歸屬,暫時逃離了苦悶。

跨度到弦樂並做出許多他們從未想像到的編曲,則仰賴製作人韓立康的幫助,這也是庸俗救星進程到二專《 Little Battle 》時重要的蛻變原因之一。
「以前我們交給製作人的作品幾乎都已成型90%。」晧宇說:「上張專輯的詠恩主要幫我們在音色上做優化,在架構不變的情況下做部分微調。」他們表示經過一張專輯、一張EP和數首單曲的磨合,彼此會做的、能想到的東西都發揮到極致了,「我們需要有另一人的美感來刺激新火花。」這是一組樂團想要讓自己作品受眾更擴圈的方式,也是展現他們不甘於現狀的企圖。於是這次十首歌他們選擇不把編曲做得過滿,就是希望激起更多變化與討論。
但沒想到首先發出驚嘆的,是話少的允祈。
「通常我會錄好幾個鼓的track給他,沒想到老師選了一個在我心中會直接被淘汰的版本。」允祈說,沒想到家耘馬上跳出來補充:「不只允祈!這件事其實很常發生在我們錄製過程!」她分享某次錄音前一天喉嚨不適,帶著未痊癒的嗓音進行錄音,沒想到卻被韓立康誇讚今天tone很好。這時晧宇也點頭如搗蒜,連忙也加入例子:「或是選了我們覺得不可能用的麥克風錄音。」他們稱這完全顛覆了原先對美感的想法,「這對我們來說都是很好的事,代表原本不曾這樣想過,但他看到了。經過這張(專輯),我們能看到的音樂畫面一定會越來越多。」

「那會有樂團跟製作人拉扯的情況嗎?」筆者追問,沒想到晧宇神情略有猶豫。
「我原本想說找了找位製作人我可以爽爽的,沒想到阿康有很多很棒的想法,反而要跟他有更多的溝通討論。加上當時有時間壓力,所以就夾在經紀人和製作人中間,真的好痛苦!」過去他和阿雷在庸俗救星中擔任音樂製作組,幾乎每次錄音、製作到混音都會到場確認,第一次嘗試讓製作人參與自己的壓力來源反而在溝通。
不過和製作人韓立康合作也讓他們嘗試了從未有過的專輯製作方式,「這次蠻有趣的是,我們樂器幾乎都是同步錄音。」家耘分享,「以前製作因為疫情,大家都是分開錄自己的部分,但這次幾乎是全員參與了全部人的錄音。」韓立康相信這組樂團的韌性與職人精神,選擇保留現場即興創作的空間,讓他們在錄音前jam出一個好的版本,再馬上進錄音室錄音,如此才能保留住一組樂團最可貴的現場氛圍感,而這是橫跨獨立與流行音樂背景的韓立康,對待許多已有明確風格的獨立樂團喜歡使用的方式。
「我和阿康很早就認識,以前很多製作案我也都會支援。其實同步錄音這件事在我之前參與VH最近那張專輯(《五常法則》)時,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晧宇補充道,「它的好處是第一製作快,第二會有像樂團的聲響,有種大家一起腦力激盪的感覺。」畢竟在數位時代,很多人會選擇把自己關在家自己做出所有樂器的聲響,有時候反而少了些隨機性。
不過這樣的錄音方式確實也勾起了他們不那麼自信的一面,每次在錄音前都提心吊膽,為了孕育那份驚喜感,製作人幾乎讓他們在沒先練習的情況下就到錄音室報到。但團員都記得當時是阿雷給了這劑強心針,說:「也是因為製作人相信我們可以做得到,才會選擇這樣的工作模式!」
願意把這些不安與懷疑自己的心開誠佈公,我想他所說的「真誠」確有其事吧?於是我們往創作過程中那些幽微的掙扎情緒摸索。
我們算是一個很真誠的樂團吧?
「最近在想,音樂對於我來說,現在(發行前一個多月)是不是做樂團最痛苦的時間點啊?」家耘率先發出感嘆,「在那之前我都處在要面對跟自己內在的衝突,像是去思考如何做好一位歌手、主唱,唱好這些歌,需要接收到別人給的聲音、眼光然後去消化…」她分享在錄〈熱海一號〉時,除了主題與親情有關,也到了創作期非常辛苦的時候,情緒堆疊難堪負荷,於是特別發了訊息給父母,分享正在錄一首關於家人的歌,同時送出一句「最近好累喔哭哭」的撒嬌訊號。
「一開始看歌名以為是很熱血的歌,是日本的熱海嗎?」筆者投以好奇的目光。
家耘笑回:「其實是一艘停在基隆的小漁船啦!因為住在基隆,每次都會看到那艘船停在港口。」她娓娓道出來源自一場美麗誤會的故事,「一開始只是覺得船名很美,然後上網查才發現它本來是要當一艘可以遠航的遊艇,但後來因為需求太少,就變成了往返基隆港與基隆嶼的通勤船。」這是第一個誤會。
做為船隻靠岸的依靠、等待遠行的人回來,這些元素湊起來都很容易將它寫成一首情歌,家耘起初確實認為是寫關於愛情的故事。「但寫到後來發現,其實比較像親情歌。」這是第二個美麗的誤會。
「這首歌詞算是我先有了頭,但寫到中間沒想法,所以就求助晧宇,讓他改完剩下的。」家耘說,晧宇點頭回應:「大概就是Pre Chorus(導歌)和第二段副歌的地方我有改吧!」
結束後家耘發現,歌詞內容延續了晧宇在〈夜歸的你〉、〈安眠曲〉等歌中展現的風格,情感呈現與其說是愛情,更偏向親情。「其實熱海一號之於我,就像家人在港口邊等我的感覺。後來才發現,原來它(熱海一號)沒有辦法走很遠,就像爸爸媽媽會乘載著你,但他們沒辦法陪你實踐你的夢想,只能力所能及地陪伴你、目送你,然後等你回家。」
其實 我還在眺望有你的遠方
期盼你 再次回頭望
牽掛著 歸來的方向
我還在原地 等著你回家-〈熱海一號〉
不過沒想到晧宇卻回應:「但你說親情蠻有趣的耶?因為我那時候聽完妳的想法,我完全是在寫愛情耶!」其實無論愛情或親情,給予歸屬感的都可以為家,這樣的誤會某程度上也是作品耐人尋味的地方。
不過這讓筆者為家耘感到開心,想到去年(2024)下半年一次專場家耘擔任嘉賓,和表演者一起分享了創作瓶頸,並在那之前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寫歌復健計劃」,現在她正用不同媒介去勾起創作動力,如今能看見她的作品在專輯中真是一件好事。
當然,持續創作的方法不只一種,他們還特地辦了內部寫歌營,到美食之都台南共同創作。
「我們其實從前年(2023)十月辦完『靠運氣不如靠腰力』專場後就馬不停蹄地給自己定作業。」家耘分享,「那時還開了個讀書會,每個人交一份對於第二張專輯想法的簡報。」如此慎重其事,是因為他們認為第二張專輯是確定這個樂團在市場上定位的重要指標。「那段時間我們其實還研究了很多獨立樂團的第二張專輯,常說第一張可以花一輩子的時間做,但第二張通常短短一兩年就要趕緊誕生。」花了些時間統整意見,並在2024年4月開了寫歌營,在社群和粉絲們互動,讓部分等待新作的樂迷安心,七月份就湊齊了一些歌。
「不過蠻有趣的事,那時候寫歌營寫的歌,最後只用了一首歌。」家耘無奈地笑著,但旋即換為興奮,「不過那些歌已經可以自成一張EP啦!」選在臺南離各自都較遠的地方共同創作,除了可以專注在創作,換個環境同樣有激發靈感的功用,只不過究竟是不是和當地食物有關?也許就讓他們之後去揭曉吧!
「所以你們寫歌營裡唯一那首放到專輯的是哪首歌?」這是必定會追問的問題,給出的答案是那首充滿活力的作品。
「這算是有目的的想要寫一首比較跳的歌,畢竟我們快歌沒那麼多。」晧宇說。而在筆者看來,這首歌正是做到生活再苦,也要幽默應對的精隨,允祈的鼓與躍著小步伐的吉他,撐起輕鬆詼諧的一面,貝斯則在底下推著人前進,主唱家耘隨著歌詞如同曼妙的舞者,在多巴胺的刺激下提領快樂泉源。
「所以專輯中的其他歌也有另外組寫歌營創作嗎?」筆者再次追問。
家耘搖頭,「後來幾首歌是我們先討論出主題後,再依據主題新寫的歌。比如說像〈你在哪裡?我去找你〉或是〈我在這裡等你〉,兩首都是晧宇寫的,另外一首〈我不想跟你結婚〉則是我很早以前就想寫和〈Marry Me〉有關的歌。」說是刻意嗎?他們同樣搖頭,雖然曾討論應該要和第一張專輯有所關聯或做出區隔,但回到現實才發現,自己能真正好好寫出來的東西,都還是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還是要經過人生研磨,但也昭示庸俗救星的作品始終能把看似懸空、難以表達的細膩情緒落地,讓聽者能感受到這是血肉之軀呼喚而來的真實故事。
「所以庸俗救星算是一個很真誠的樂團吧?」晧宇給出答案僅有肯定的問句。
談完樂團蛻變、創作中還原出來的故事後,生活何止如此?
也許我是相信它有結果,才按耐得住這些痛苦
採訪當下,他們細數身邊有三個生命離開,事後更得知,當天經紀人缺席是因為需要陪伴癌末的家父;而採訪結束不久後,晧宇也抱病住進了醫院……其實,《 Little Battle 》有大半篇幅都潛藏著對生死離別的感悟,但這些沉重的事情他們不願透過音樂直白地說出口,反倒願意用「時間」一詞來定義一切。
時間
不為不為不為不為 為我停留
才發現 眼淚都為自己流
一首直白表現「時間」的歌,被阿雷笑稱聽完也大概浪費了3分鐘。說點煽情的話,他也許只是想沖淡一點對時間流逝的焦慮吧?但小至〈拖延症*〉,大到追尋永恆的〈有效期限〉,無不對有限的事物感到沮喪。
「我覺得分別就是會讓你重新思考時間這件事。」晧宇小心地使用詞彙來表達那些心底話,「有時候你會覺得跟一個人相處就很平凡、很日常,但當發現相處過程中開始有了一個數字在倒數時,會覺得很多東西很遺憾,然後很多時候很珍貴。」
這首是筆者越聽越得己心的作品,想必是信仰,促使他以歌頌之名贊遍眾生萬物,只希望求得永生,因為:
「讚美主的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使徒行傳13:48》
「這是最貼近我近況的歌,就是要珍惜每個日常、每個當下。」晧宇說:「它大概就在我寫完〈你在哪裡?我去找你〉和〈我在這裡等你〉之後創作的。當時看到一句話:『平常我們不會去在意離別,但當你發現真的要道別時,就會發現一切都很珍貴。』可能以前很在意的事情,在你人生中就是那麼地渺小。」
讀懂了珍貴,因而恐懼道別,於是渴望永恆,相信只要是能意識到生死的個體,多少都會對死後充滿未知的惶恐,希望它別親臨面前,而晧宇更把這份思緒投射到連千年晨星都為之感到焦慮。
有效期限裡
仰望星星的你
還不知千年晨星
也奢望永遠年輕-〈有效期限〉
「30歲以後,其實會發現時間越過越快。長大後很多小時候的快樂已經不能滿足你的原因是什麼?就是開始覺得那些東西就是在浪費時間。」晧宇說:「我其實是個焦慮感很強的人,覺得不精進自己就會被甩到後面,所以我忙碌地工作、忙碌地想,簡單的快樂已經沒辦法獲得滿足,要等到身邊哪個人走了,才會發現原來彼此之間珍貴的小片段已經不見了。」
他把自己平時潛藏在嘻笑底下的真實情緒扯了出來,說自己習慣累積情緒,心情先放一邊,努力做很多事,但到了專場往往是那個最愛哭的人,「我的情緒就是這樣,通常在表演或是在講自己創作的某首歌時,那些情緒就會突然跑出來,那是我唯一可以分享比較真實狀況的媒介。」
這才明白晧宇的Little Battle,其實是在對抗時間所產生的焦慮,以及定期需要釋放的情緒。
而比起晧宇擅長將生活體悟灌輸在創作中,家耘有些時候則會小心地把相反的情境用在不同的經歷上,在時間的考驗裡,有些事會重過程,也些則會篤定某種程度上會有好的結果。
「其實在製作專輯這段時間,很多外在衝突是不可抗力的。」家耘說:「比如票房、專輯時程快來不及或生活總會發生一些變故,很多時候自己很無力改變,但又會繼續下去。因為我知道庸俗救星他不會是沒結果的,你可以知道這個痛苦只是一個過程。所以音樂對我來說,我是相信他有結果,才可以按耐這個痛苦的過程。」
而看待生活,家耘反倒能接受「沒有結果,但過程很美好」的事。
「它和〈Marry Me〉剛好相反,你知道最後結局會是一團糟、是個不對的選擇,但是因為你跟他相處的過程太美好,所以選擇忽略那個可能讓你傷心的後果。」家耘分享。
會沒結果嗎?至少在本該一成不變慢慢走向分離的路上,嘗試拿回一點自主權,去多做一些縱使徒勞,過程卻有意義的事情吧?去挑戰、去抉擇、去感受失去或體會遺憾,然後相信結果是好的。所以,要說《 Little Battle 》是張受詛咒的專輯嗎?筆者也許更願意認為他們在「輸得徹底,卻意外贏回了生活」後,還能一如既往地走在自己目前的信仰路上前進。
「哇!突然發現我們剛好在你們壓力最大的時候來聊天欸!」筆者說,訪問到尾聲,他們多少有把當下的苦水好好宣洩一番。不過緊接而來的是為專場售票、為重新練好十首新歌而焦慮。
「重點我們這些歌都還沒跑過!」晧宇哀號。
「但這些歌我們在錄音的時候有跑過啊?」阿雷回應。
「早就忘記啦!」晧宇說。
「那時候根本憑著一種魔法在彈!」家耘笑說。
「不過上次在排歌單時算了一下,其實庸俗救星很屌欸!我們現在已經有大概快30首歌了!現在要去演小巨蛋完全沒問題!」晧宇又回到平時嘻嘻哈哈的模式。
看來他們又走進了日常生活各種小挑戰中,繼續寫歌、生活、唱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