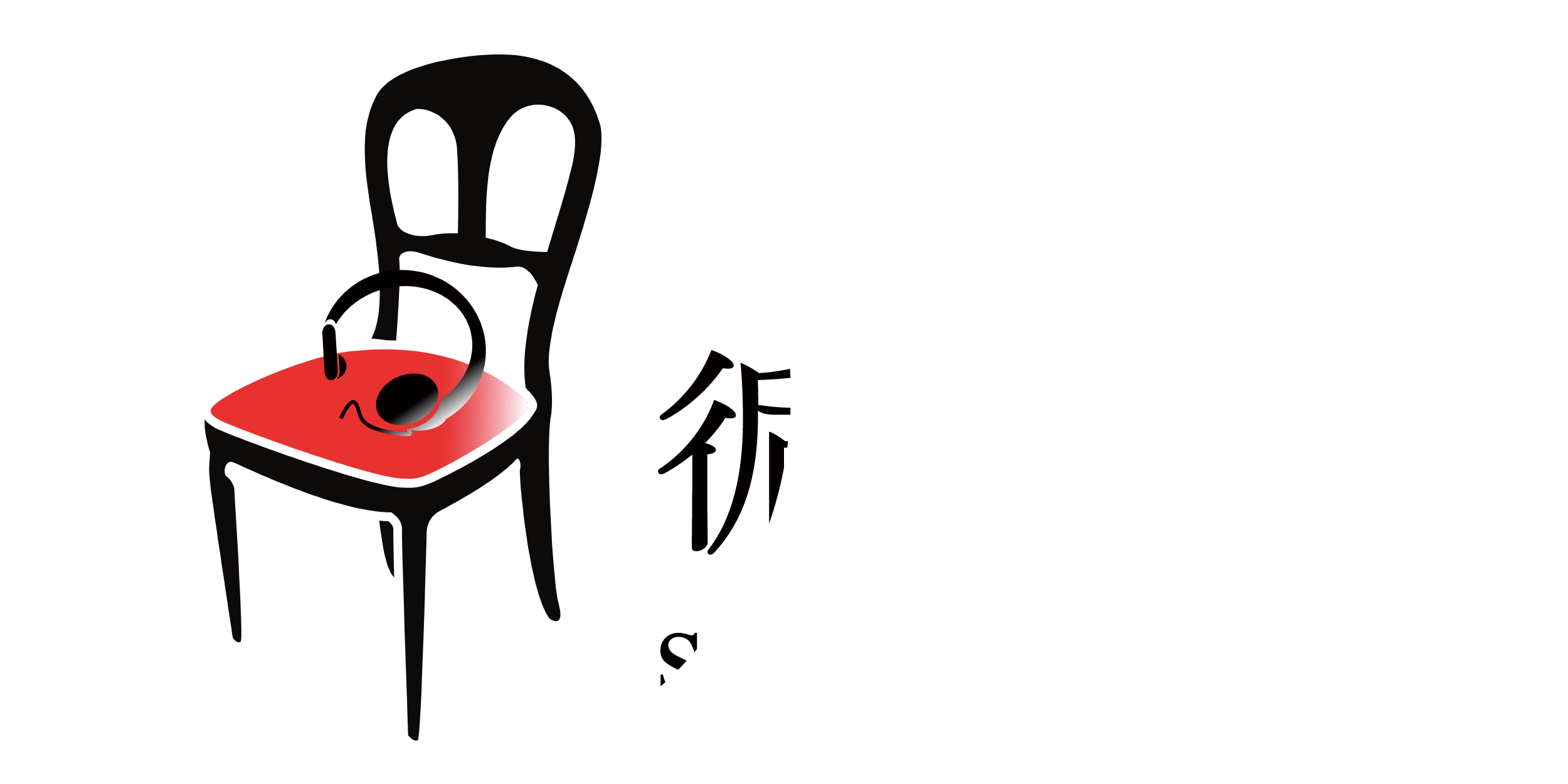《圓缺》專輯上架那天,鄭宜農也同時辦了專輯同名演唱會。
猶記專場第一首新歌〈歹物仔〉後段她手持大聲公,意不在登高疾呼,反倒跳進背後由樂手們編排的細碎聲景中,模擬了各種笑聲、細語。她說這首歌和樂手們練了三個小時,難度極高,同時也是第一次首演,挑戰意味濃厚。
時間拉回演出三週前,採訪時筆者問宜農,這張專輯耐聽程度是否會和上張《水逆》一樣?「我不確定。」她說。會擔心嗎?「一開始有,但現在就覺得『煞煞去』啦!」她露出燦笑。隨後,筆者提了關於「圓缺」的開放性問題:
「那麼,這張專輯出來了,妳還會覺得過程或哪裡不完美嗎?」
「沒有。」宜農回應地快速且堅決,不過旋即接續說:「應該說,我那時看到這個訪題時覺得非常有趣,就是這張專輯本身就在講人生的不完美,所以如果你要說有什麼東西不完美,那不就是『很完美』嗎?」
在聽完鄭宜農用著幾乎字句斟酌,最後說出認為最適合也最讓人能理解的話,來回應筆者每一道對她及《圓缺》的好奇後,知道她對於目前的創作狀態已了然於心。
我想,她說的是對的。

從過去專輯以星球為命名,再到《水逆》走上一條向語言發問的道路,五專的《圓缺》對鄭宜農來說,不管是觀察問題的多面性、選擇詞句的精鍊性、甚至是實驗音樂的前瞻性都向前再跨了一大步,持續在強化語言和電子樂共容的現階段目的上,謙卑地投石問路著,無疑已是位臻於成熟的音樂創作者。
再次「問」出來的專輯
「在創作過程,其實同時會有社會性跟動物性思維,比如前年的《金黃色三部曲》,它是來自於一個非常感性的瞬間,但可能寫了一兩句後,很快就會變成理性整理。」
宜農針對筆者在專訪伊始,拋出了從2023年自立門戶後推出的《金黃色三部曲》,似乎和這次專輯《圓缺》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她反而以小喻大,點出從單曲到系列作品那段模糊卻讓人玩味的關聯性。
回頭來看這段關聯,她給出自己心得:「我覺得比較像是一氣呵成地把我近兩年的狀態像壓縮包裝一樣,很密實地把它做出來。」包括這次《圓缺》擁有完整的企劃性;過去專輯皆以星球、天體現象為名等,後人來看似乎有意為之的事,還原創作當下大多還是無心插柳。
「這件事情很奇妙,創作的過程中會邊整理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創作者。我認為即使現在很知道要怎麼去做一個完整的概念論述,甚至一開始就想好我要寫十首跟缺憾有關的歌,在寫歌的時候還是不會想到他們彼此間的關係。」繼續向源頭發問,宜農緩緩道出肯定好好思考過卻再正常不過的核心,說:「我平常喜歡閱讀、思考跟朋友討論,從開始寫歌到現在這些習慣並沒有改變,所以它可以很自然地長出一個樣子,不會偏離我關心的事情太遠、不會偏離某種說話的節奏、使用詞彙的方式。我發現這些從日常生活中建立起的創作方式,再去發想任何主題都會跟彼此很近。我覺得事情是這樣來的。」
「例如妳的創作都希望有些距離感地去看待事情?」筆者接著問,將焦點從作品概念再回推到創作本身,而這也是不少人發現並會向宜農提問的事情。
「我覺得寫情感,尤其是描寫悲傷,最難的地方是要讓它還有空間,而不是在耽溺的狀態。」鄭宜農說,「我認為真正觸動人心的東西反而是在你沒有講滿的時候。」
「甚至結局可能也是放空?」
「是!因為我覺得好的作品是問出好的問題,而不是畫下好的句點。這是我個人的執著。」話畢,宜農勾起對這樣的回答連自己都滿意的微笑。在資訊吞吐過程,吸納是其一重要,透過創作反芻、理解自己是其二,漸漸形成鄭宜農如今的美感表達。
於是在《圓缺》之前,向天拋出了萬古難解的疑問。
寬寬仔來到祢的面前
所有的智識攏不足來了解祢
鄭宜農說,這首歌是她各式各樣提問裡面,問題尤其大的。人是什麼?人的世界長成現在這個樣子是為了什麼?直到現在仍偶而縈繞在她腦中,「有時晚上睡前就會想到近期社會上發生的事,也不會總都能平淡地看待這一切。」但能問誰呢?帶著這樣的疑問寫成歌曲後,她發現最後能問的只有神,但神是什麼?是自己內心的倒影?或是人們集體的意志?這些問題都像在虛空裡找答案。
「所以,真要說有什麼結論的的話,那個結論可能會是『我們人類最大的謙卑就是要理解到不是所有問題都有答案』。」
這樣的自問、從問題找解答並試著能自洽,卻發現這些問題不是無解,就是沒有絕對答案。試著溯源才明白,其實從提出問題的當下就已有數條供選擇的道路,它會隨主觀意識走向某一個解答,認為看出去的世界該是如此。但宜農不願耽溺於此,這時在創作上試著將視角保持一定距離發揮了作用,讓她總能在一個主題上延伸出雙向或多面向思考,那麼結局的開放或無解在作品中自是常態。
「我在寫詞的過程中都會想去找到這個雙向性。這件事其實不止出現在《圓缺》,只是這張專輯尤其明顯,可能因為我玩出心得了吧!」宜農笑稱,表示會想到專輯主題「圓缺」,本身就和雙向性有著很大的關係,因為這就是她一直在消化的事情。比如提到傷痕,有試著要擺脫傷痛記憶的〈真罕得想起來〉,同時也有要與那道傷共存的〈留佇咱的血內底〉;又如〈未曾準備好〉跟〈牽我〉都提到陪伴,前者失去了這份陪伴感,後者則講述擁有陪伴的親密經歷;再如〈又閣減一工〉說得是時間的有限性,而〈一寡時間〉則是必須要給彼此一段時間才能相互理解…這些作品都被更純熟地服貼在專輯裡,成為專輯核心概念下的歌曲編排。
既然歌曲之間安排了不少對比,那在音樂上呢?

語言和電子樂交織的肌理
〈寬寬仔來到祢的面前〉是鄭宜農與南韓創作歌手李瀧的首度合作歌,兩人關心的社會主題接近,但創作方式卻大相逕庭,合作過程產生了不少火花,「李瀧會用非常『實』的方式去寫她對人類世界的情感觀察,而我自己所有寫的歌都很形而上。」宜農這樣形容彼此。之後,李瀧果不其然丟了一個角度完全不同的歌詞,但她懂李瀧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在台韓文穿插之間,默默形成了對話。
不過在編曲上卻劇烈拉扯了一番。
細聽李瀧過去的作品,她在處理相對龐雜的議題時,不管是表達出底層人民在貧困與不平等中反抗的〈狼來了〉,或是用麵包做為對消費文化批判象徵的〈吃了麵包〉等,都使用了民謠,或以真實樂器呈現溫暖形象的編曲方式進行。這與鄭宜農以電子樂做為專輯的主要聲響選擇有著天壤之別,以至於當時李瀧聽到這首歌的編曲時相當無法接受。最後鄭宜農和製作人Chunho經過討論後做出了調整,讓這首歌前半段仍有電子聲響,但到了中段李瀧聲音出現時一轉畫風,改以木質調樂器做為主基調,不過也因為這樣的調整,讓彼此的對話感更為明確,這是在李瀧刺激下所做出的權衡。
「其實這一整張專輯有非常多我和不同人之間的平衡,不管是一開始自己編得民謠感較重,或甚至有一點搖滾,但最終還是把它統整成一張電子樂專輯,所以仔細聽的話應該都會聽到一些拿捏的痕跡。」鄭宜農表示,《圓缺》在聲響的統整性上比以往都還高,目的就是要聚焦在語言跟電子樂之間的關係。不過這樣的堅持,也讓當初在製作過程時,常常在「命案」邊緣。
例如〈未曾準備好〉原本應該會是一首dream pop的歌,最後卻成了Synth-pop(合成器流行)。
「這首歌原本我已經編得很完整,自己也非常喜歡。結果最後丟給製作人,再回來給我的版本卻完全不是原本的樣子!」鄭宜農說,眼神中還能感受到當時的驚訝與氣憤,不過隨即也緩和了下來,「但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他要做這樣的更改,畢竟要讓專輯的統整性夠高。」
「只是我在聽到瞬間還是很想把他掐死!我覺得我原本編曲很棒!不知道為什麼要改成這樣!還是有這樣的心情。」宜農補的這句回馬槍很真實。
「這樣的心情常出現嗎?」筆者追問。
「其實出現蠻多次的!像〈真罕得想起來〉本來我也是丟了一個很完整的版本,那版本我也覺得『天哪!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作品!』但他最後做出來的版本比我還兇100倍。」宜農接著說,「但怎麼講呢?這不是遺憾、這不是不完美,只是做了不同的選擇,而這些選擇沒有不好,所以我也愛現在的選擇。」
她的玩笑是真的,掙扎也是真的,最終愛她現在的選擇也是真的。儘管這樣的拉扯偶有所聞,但仍未偏離軌道,依舊在那條道路上行駛。當然一同前進的,還有語言。
《圓缺》演唱會上半場,宜農在中間talking環節以字代話,無言之中,僅有手機打字聲,用投影在大螢幕上的對話框與觀眾互動。隨著越到後面字跳得越多,甚至出現詞不達意的語言時,畫面戛然而止…
「語言有它的極限,是這個極限讓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沒那麼簡單。這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語言,但我們其實彼此並不理解。」鄭宜農說。
在她的創作裡,已漸漸能適應華語和台語共同存在,而這些語言同時保藏著珍貴的文化資產與人類歷史的傷痕,面對這樣複雜而龐大的系統,使身為創作者的她在挑選主題和書寫上始終保持敬重之心。但重拾語言對鄭宜農來說仍是藏不住的喜悅,因為對文字的摯愛,讓她在咀嚼的過程中,願意捱過沉潛學習、請教專業,再以律己的方式進行輸出。
「之前是真的花很多心思在修改(台語)歌詞,但這次修改的點不一樣了,比較像是什麼樣的詞更好,已經是下一個層級的事了。」經歷上一張專輯的台語洗禮,鄭宜農這次邀請朱頭皮、Ciacia何欣穗、吳永吉(吉董)擔任台語協力及台文指導,自然相當嚴格,但在寫詞上也越來越游刃有餘。
「所以妳再回到華語創作時會比較輕鬆、文字更精煉嗎?」筆者詢問。
「確實會比較快啦!」宜農說:「不過這很有趣,我現在寫華語歌的嚴格程度也跟以前不一樣,台語教會了我一些事,而我再把這個邏輯套用在華語上。」她舉例詞曲咬合,在台語的語境下會被要求嚴格遵守,但當把這個習慣應用在華語後,發現每一句聽起來艱澀的話,唱起來卻變得更好聽了。鄭宜農更進一步舉近期她寫的華語Hit Song〈如果你也想起來〉為例。
「它乍聽就是一首流行歌,但其實我在寫詞的過程中,有把這東西(嚴謹的詞曲咬合)套用進去。所以會發現這首歌的曲式是迂迴、不工整的,是因為要順著我寫的詞,因為我想要把詞講好。」宜農表示,自己現在用任何語言創作都會特別刁,而華語只是因為相較熟悉,創作速度才快。
到了近年,鄭宜農更想把語言玩得更深,選擇現代人少用的詞進入她的作品中,「好比一個簡單的主題,你在裡面用了一個很難的詞,如果可以很聰明、很漂亮地講出原因的話,那我就會用它!」她分享最近一次嘗試便是〈未完待續〉這首歌,首次使用了「濫觴」這個詞,既有古味,也相當精確。
「我真的太喜歡創作了!只要把字用得好、做出反差的話,那就會是個好作品。」
語言和電子樂是現在鄭宜農的進行式,在把這些武器磨利、技術走向精緻之後,下一階段便要鋪上真實的血肉。
我想寫扎實的疼痛、扎實的失去-扎實的血肉
一切的起因,來自筆者觀察到的一件事。
「我發現妳在好幾首需要面對龐大問題時,都會使用類似『血肉之軀』的詞來形容人耶?這是妳這段時間的創作習慣,還是希望刻意呈現?」比如,《金黃色三部曲》中的〈咱〉:「你看 遐是規塗跤的血佮肉」;〈留佇咱的血內底〉:「過去 流佇咱的血內底」;〈寬寬仔來到祢的面前〉:「我無啥物通保證 只有一粒 肉做的心」等,除了新作,也橫跨到了2023年的創作場景。
「這件事情我是有想過的,我想寫扎扎實實的血肉。」宜農聽到筆者的觀察很是欣喜,繼續說:「現階段對我來說,雖然總是處於形而上的狀態,但我不是沒有感覺到這些東西。現在的我想要寫那些扎實的疼痛、扎實的失去和扎實的獲得。它會出現在講集體意識的歌裡,但詞彙我想多使用一些真的會感覺到痛的東西,像是肉被捏的感覺,不是在作夢。」
鄭宜農形容,就像平常看電影時,最厲害的地方往往都在很日常的片段,可能僅是單拍肢體、皮膚、表情或人與人碰觸的瞬間鏡頭。「它們背後可能都有很多意思,我覺得創作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找到那個意思,就像如果大家能讀到這個血和肉背後是什麼,那對我來說就是成功了。」
就如這首歌所述,真實的血和肉,背後是人類在歷史上不斷輪迴、無法消停的族群戰爭,這些傷痕,因為影像和發行時間綁上了228事件這道歷史大瘡疤,但其實把量體縮小,依然可以單純是一首有流行基底的失戀歌,它依然可以扎實地形成痛與失去。
宜農的作品就是擁有可大可小的維度空間,給聽者自行揉捏的想像。
而另一例,我們聊到了放在專輯後半段的〈一寡時間〉。
佇開始 失去體諒以前
開始討厭家己以前
佇開始閣一擺 毋願再面對進前
「在我聽來,這首歌很像妳在針對最近社會的紛紛擾擾,期望去做到的溝通是嗎?」筆者說,沒想到宜農彎起笑容,有些狡猾地說:「我跟你講一件很奸詐的事,就是我不會正面回答這題,因為我覺得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
「畢竟〈一寡時間〉完全可以用來講感情。」沒辦法,我只能投降,但對於這首歌給予自己的療癒很真實。於是繼續和宜農分享:「其實在看完這首歌後,我聯想到過去妳寫的一首歌〈就算我放棄了世界〉,因為它的結尾同樣讓人覺得,這世界縱使糟到沒辦法變好,可是還有你會陪伴、鼓勵我。」
但我想牽你的手
但我想你一起走
但我想牽你的手
就這樣吧
不需要 困惑-〈就算我放棄了世界〉
請你相信我
咱只是需要 一寡時間-〈一寡時間〉
說實話,那是筆者對鄭宜農最深的印象,私心來說,這樣的歌也曾拯救自己無數的夜晚。而宜農靜靜聽完後,還未正面回覆,反倒提起了另一件事,她說:「其實在人類世界中,公眾人物是一個非常違反自然的存在耶?沒有人原本就需要知道這麼多、需要被這麼多人觀看,也沒有人可以影響到這麼多人。」
「也沒有人可以一次受到這麼多傷害。」筆者跟著補充,宜農點頭同意。
「我們人被設計出來,其實並不需要面對這些東西的。」宜農話鋒一轉,回到了主題:「所以關於陪伴,或者是關於任何與人建立關係這件事情上,我常常會跟我的聽眾講『我們就看緣分』,出新的作品時,有多少人願意在這樣作品停留多少時間,那都是緣分。你覺得需要的時候你就來,可是一段時間後你覺得不需要了、你成長了,或者是你現在需要的是別的東西,也沒有關係,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這樣子想的。」
「我不覺得有任何一個人應該要永遠抓著自己的身份不放,或者是永遠在同一個舞臺上。」鄭宜農說,如果到了某天,自己的聽眾開始變少了,開始有新的人出現,那她也會很自然地退居到另外一個地方,這很正常。「所以這樣的態度會出現在我任何的作品裡,講到任何情感,縱使再濃郁,尤其關係到陪伴、與人對話,或很親密地訴說一種情感時,我最後一定會留一個『但是沒有關係』。」
鄭宜農最會寫情歌了。尤其在〈牽我〉這首歌,可以說是這張專輯的情歌代表。
我有我的 你有你的寒冬
我有我的 你有你的惡夢
我有我的 你有你的深深的孤單
我袂驚 只要你 牽我
「這首歌乍聽之下邏輯很怪,它完全不是一首很正常的流行歌,聽起來可能很抒情,但它的吉他拍點毫無邏輯,但不知為什麼這麼怪的拍點,築起來後卻又變得這麼合理。」鄭宜農說。
回到了專訪開頭,聽了那麼多故事,這張專輯完美在哪呢?
「因為所有的不完美,到這張專輯就變得很完美。」鄭宜農繼續說:「因為這張專輯就是在講不完美,所以沒有什麼遺憾的地方,不過實際上它真的很精密,這張專輯很真,也很高級。」
圓缺之後,不是終點,反而走上開始
《圓缺》是鄭宜農自2023年成立公司後自營發行的首張作品,如同她們的公司名「邊走邊聽」,月的陰晴圓缺同樣也不斷變動、前行著,而來到專輯概念,不管是台語創作、使用電子樂似乎有某種目的性驅使著她要不停前進。這種「道路感」是整張專輯聽下來會留下印象的訊號。
「我認真在想你講的道路感。」宜農回應筆者的話:「確實這整張專輯到了最後一首〈圓缺〉算是統整整個音樂的結尾,而最後一段有大概一分多鐘的純演奏段落,它從很電,到最後會突然出現笛子,其實我們確實在用聽覺去創造一條新道路,你要說是輪迴,或是在一片黑暗中突然出現的那道光都可以。我們可以往前走了。」
《圓缺》是一張不斷在往前走的作品,但它並沒有走向結局,而是開啟新局,聽完後回到〈真罕得想起來〉,再次進入重複循環。《圓缺》也是一張在不完美定義下相當完美的專輯,它有著音樂人們共同協調、拿捏權衡的影子,卻能展現最真實、精密的高級唱片工法。而做為台語專輯的《圓缺》,已能順利跳脫語言束縛,找到那些微觀、宏觀都可訴說的切入點,有距離地觀察著這個世界,赤裸呈現人們永遠的缺憾。
攝影:三倍(@baaarnettt)
採訪場地:現流冊店 hiān-lâu tsheh-tiàm(@hianlaubookstore)
特別感謝:邊走邊聽有限公司、Fantimate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