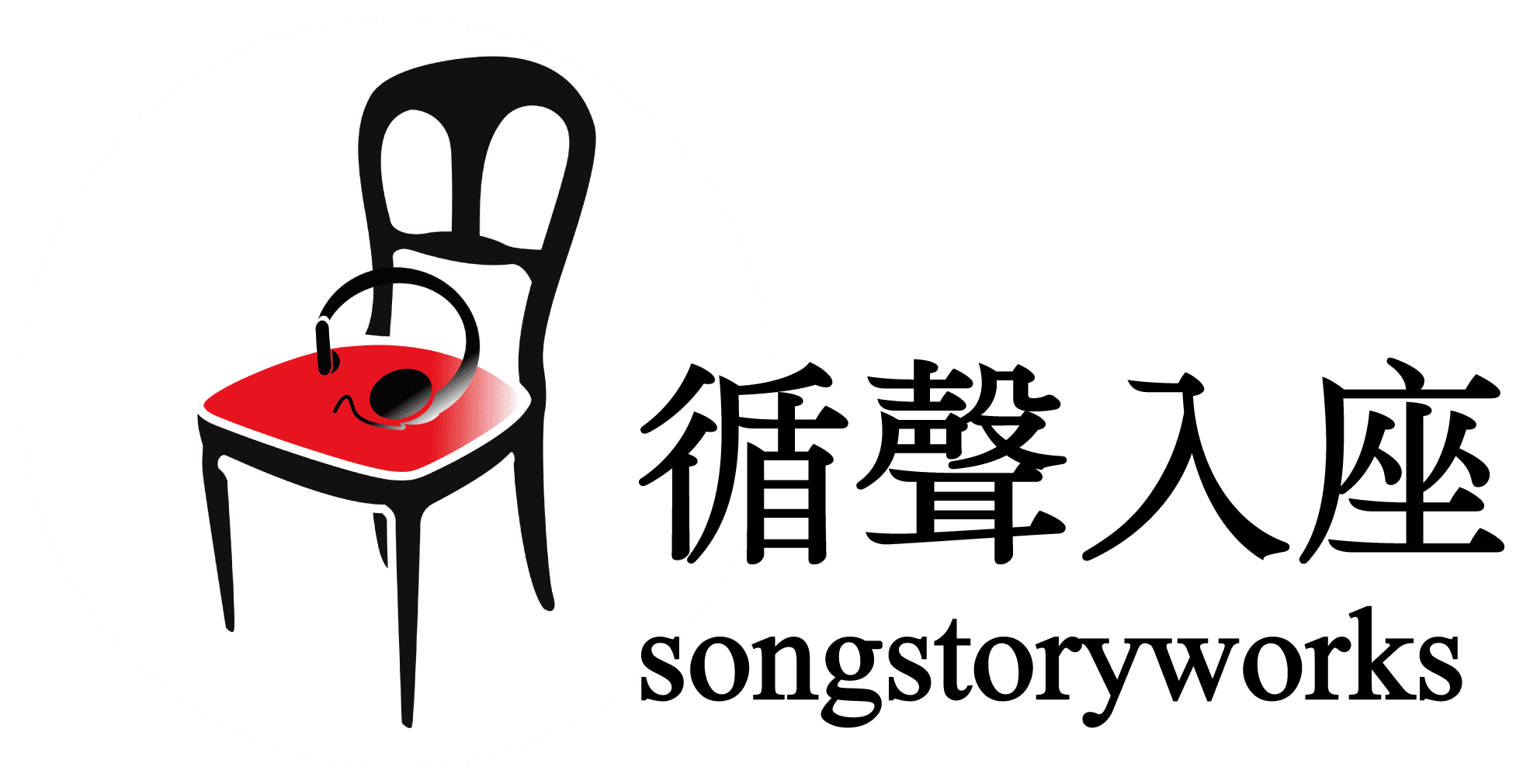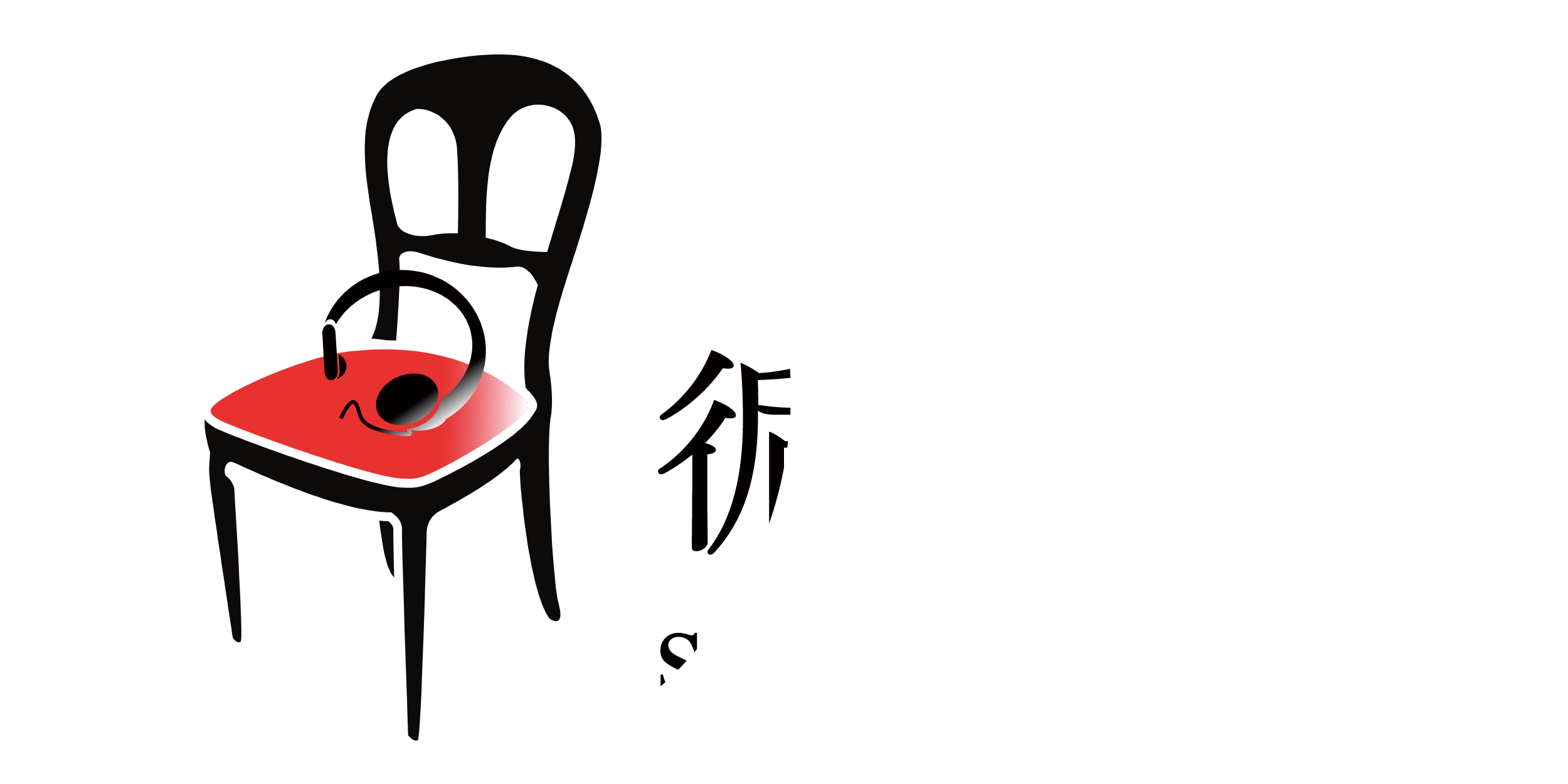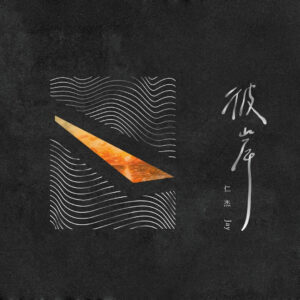去年(2024)5/20於第十六屆任總統暨副總統就職晚宴上,李竺芯著一襲紅色連身禮服唱起了數首經典老歌,但唯獨一首新歌,是她以自身出發,從台南、台灣再向世界,用台語唱出了那句「台灣的查某囝」。
其實從那場國宴中不難看出她富有才華的一面,唱鄧麗君〈甜蜜蜜〉時,展現李竺芯精準且擁有多年歌唱基礎的嗓音;與AI文夏老師合唱的〈黃昏的故鄉〉、〈晚安台灣〉合音及台語歌唱自然在她的守備範圍;而選唱客語歌〈花樹下〉更是證明她跨語言的能力。後來同年年底,這首〈台灣查某囝〉正式被收錄到李竺芯的首張台語專輯《Suí 水》裡當作收尾曲。如果只聽過單曲,與收錄專輯的誠心推薦版相比最直覺感受,應該會是將原先的彈指、鋼琴的音樂鋪排全轉換為木吉他與弦樂,對應歌詞「人若聽著我一開喙 講有溫暖的古早味」似乎可以合理解釋她讓詞意和音樂的咬合更緊密。可深入了解並聽完專輯後才發現,那是從「美」去定義自我與群體認同的過程,相對完美與成俗,鬆綁那些性別與語言所帶來的既定印象,才是讓作品得以樂音豐沛、輕鬆還俗的原動力。
本篇將點出《Suí 水》專輯合理具備輕鬆活潑與巧施文化挪用的原因,以及介紹從歌詞延伸而出的女性書寫、性解放與跨語言諧音等重要專輯元素,期盼在輕鬆聽歌之餘,也能體會作品中散發出的魅力。
技術完美,卻用創作發洩人的不完美
那麼,李竺芯是誰呢?她的音樂底蘊師從這位過去經手江蕙、阿吉仔、陳雷、豬哥亮等台語流行歌手的詞曲創作人-陳宏老師,採日式傳統師徒制訓練,因此從小便待在需要專注完美的音樂環境下。令之後初次與她合作首張專輯《和昨日說再見》,同樣堪稱現代金曲製造機的製作人柯智豪,都驚嘆她的唱作實力。

不過在一篇專訪[註1]中,柯智豪也提出了憂慮:「竺芯就是太會,但時常藝人很重要的『本心』就會被這個長年的厲害掩蓋,久了連自己也忘記。」側面點出首專製作過程的李竺芯,她的匠人之心、藝術家身分皆已有,但唯獨身為自己的創作靈魂還在拾尋。當時柯智豪為她的作品上色,盡量將她拉在年長者和青年人都可以接受的位置,讓她放心唱自己的歌。
再後來大概到2022年,大疫之期可能給了李竺芯許多沉潛、梳理的時間,漸漸能看見她在社群平台分享有關創作、生活等長、短篇文章,更在當年底和朋友試做了podcast節目以女性視角談日常,為正式迎來上升期的2023年鋪路。
她定義2023是自我蛻變的一年,參與了許富凱《五木大学》專輯的單曲製作、透過陳珊妮介紹,參與了K6劉家凱的首次個人專場。而最重要的,是參加了《音樂主理人》電視節目,讓她贏得了更多觀眾與音樂人的目光。與NIO合作的〈瘋后〉證明她的舞台魅力、初登場的〈拌拌咧〉更是亮出她磨了數年的創作刀鋒,令眾人為之驚嘆。而對她來說相當重要的作品〈台灣查某囝〉在當年十月誕生,似乎找到了創作核心位置,開始輸出女性視角的作品。
這段過程,驅使著李竺芯在擁有技術、才能之餘,也有了想說自己所關心議題的動力。於是以跨語言諧音這需要創意才能輔佐為盾,透過女性書寫與大談性解放議題為矛,邀請金曲音樂家鍾興民老師共同製作,形成《Suí 水》這張不拖泥帶水、擁有清楚輪廓的專輯。
我先是查某囝,才是台灣人-專輯中的女性書寫與性解放
李竺芯曾在一篇貼文和友人討論〈台灣查某囝〉中,點出了創作原點:
「這首歌妳寫的是什麼?」
「我啊,這首歌就是我。」
「那會不會,重點其實不是『台灣』兩個字,是『查某囝』?」[註2]
在以專輯為篇幅,想要討論較大議題前,最一開始都會是在身邊出現許久的問題,她想解決,於是從問旁人「妳覺得我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模樣最迷人?」開始驅動產生專輯《Suí 水》中的重要命題,點出了女性的自我審美觀,從而延伸出性別議題,再到友人看出了作品像是「對台灣女人的疼惜」,點出了以女性為主角的文化反思。
筆者認為歌詞這句「有時陣慣勢共家己放咧後壁」應為重要契子,如此才闢出專輯其中一條以女性視角書寫的路,甚至往性解放方向前進。不過這句歌詞僅反映了父權社會下兩性關係中的女性多習慣以「依附」、「難以獨立」的觀點進行直覺思考,覺得該「犧牲」、「成全」才是婦女的美德。直到了這句「溫柔的驕傲思想的堅強」才稍能感受到面對困局時,終於決心「出走」的心態轉換。但李竺芯在專輯中並沒有要反覆實踐從「依附」到「出走」的路線,畢竟「脫離依附活出自我」這件事應該在民初張愛玲、丁玲、蕭紅等作家作品中,因為社會環境關係才會大量出現[註3],如今台灣對性別觀念更加開明,就可以像李竺芯一樣用更自然的方式,書寫女性視角的日常。例如:〈懸踏仔咬跤〉(高跟鞋咬腳)就以女性穿高跟鞋不合腳,來形容感情中會面臨的考驗,甚至將穿高跟鞋會造成的身體症狀都入詞,雖緊湊的電子曲風帶來緊繃的氛圍,但看到歌詞還是會不免嘴角上揚。
「跤麻手麻肢體痛疼 腰疼心疼坐骨神經疼 若久就齷齪縛手縛跤」-〈懸踏仔咬跤〉
另一例子則是〈荷爾蒙〉,它配合著經期來影響女性的日常與情緒,卻也令女性充滿致命吸引。編曲搭配歌唱側重性感,而不規則的節奏拍子則是隱藏在暗處準備給女性一拳經期來潮。
「嫉妒嫉妒 because of my 荷爾蒙 快樂快樂 because of my 荷爾蒙 起起落落 because of my 荷爾蒙」-〈荷爾蒙〉
除了聽來趣味的女性視角作品外,李竺芯更往性解放方向試探。這在過去的女性主義上是極左的光譜,認為要實現完整的男女平權,更應該拔出「性」在傳統女性的感受上會下意識感到壓抑與低下的感受。早在1997年,由台灣婦女運動先驅之一何春蕤的著作《呼喚台灣新女性:豪爽女人誰不爽?》中便提及:
「身體和性領域中的價值觀以及實踐的根本改變,不但相關女人個人的愉悅,更深刻的影響女人的主體養成、女人的自我掌握和力量、女人彼此之間的微妙對立關係…」[註4]
二十幾年後的現在確實同樣開放許多,但在仔細讀〈Sakura Gansha〉的歌詞時,仍會覺得前衛與直白(可見筆者道行還不夠)。
〈Sakura Gansha〉是日文羅馬拼音,中文翻做「櫻花顏射」。李竺芯特意打破了「顏射」一詞的男性本位,轉換為主旨「女性的性歡愉應該由自己掌舵」,因此歌詞中大量地以日文記下這些狀聲詞所代表的聲音。透過日本演歌的形式,創造出一首潛藏許多,放招時才華盡現的性解放作品,是專輯中極具看點的歌曲之一。
回到了專輯主旨:「何謂美?」這是在女性書寫上避無可避的問題。當然,創作者大可以輕描,說著不管美醜都是一種美,讓讀者仍帶著各自成見繼續生活。然而,李竺芯顯然不就此放過這難得的機會。形式上,她以〈阿美蝶〉做為引,文字上用「這个花園有紅有青有各種美麗」打散既定的美,透過編曲製造穿梭不同場景,代表遍地美不勝收,小心意亂情迷。
接著來到主題〈水〉,編曲上採大量調變、以Sample堆疊人聲製造科技感,來呈現「怪美感」。而在文字上實際處理了各種對美的疑惑,首先拋出「啥物號做媠 誰講了有道理?」,再以瘦美、自信美、長輩認為的可愛、豐腴、平胸、陽剛、陰柔、天然的、醫美過的…等,其中更反轉了台語諺語「媠䆀無比止,愛著較慘死」(美醜沒得比,愛到就死定),在歌詞中改寫為「媠䆀無地比 愛著家己上媠氣」(美醜沒得比 愛上自己最美麗)。更邀母親錄音,說出:「哎唷阮這个乎,阮這生緣較好咧生媠啦 今仔看䆀䆀仔,啊毋過愈看愈古錐啦」,企圖用過去華人愛用的謙詞,來翻轉現代女性的自我審美觀。
美不該定義在外表、單純的所見所聞,而應該是從自身各種感官中散發而出。而最能留下來的,便是你說的那些話,這是筆者認為專輯中最重要的觀點。
接著讓語言展翅高飛,透過不同語境文化,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考觀點,增添專輯中的趣味性。李竺芯在專輯當中運用了不少跨語言諧音,適時鬆綁單一語言的侷限性,同時也增添更多的可看性。畢竟,誰能不愛諧音梗呢?
文字與音符的協調,跨語言諧音的正向驅動力
近期在李竺芯的社群平台開啟了系列《足芳足芳台法課》,引起了不少人關注。她在貼文中分享,這源自許效舜在《鐵獅玉玲瓏》的其中一個把台語說成法語的段子[註5]。過去關於法語和台語相關聯的文章不少,除少部分如麵包(法文:Pain)是經日治時期傳入台灣外,大部分只是正巧音近而連結並產生趣味。這種利用類似音,讓聽者產生不同意義的聯想,便是諧音的其中一種用處。
而李竺芯在〈足芳足芳〉中則是下足功夫,特意挑選法文中的小舌音[r](輔音),找到了台語中的「屜仔」(thuah-á)、「拖仔」(thua-á)以及「蚶仔」(ham-á )、「蝦」(hê)兩組字,前者因[r]發音原理僅是讓小舌輕輕顫動帶過,而台語中的[á]雖語調重但同樣氣短,所以在發音上可以做到一點銜接;而後者在法文中雖並無英文的h音,但因為法文的[r]近似ㄏ(喝),對應台語[h]的發音(僅是讓氣流通過,並不促成發聲),同樣可以做到些微銜接。當然,這裡指的「銜接」是要在不那麼精準要求發音的情況下,將這些發音偷偷以小舌音[r]來替代,念起來很像法文發音。不過筆者認為最主要還是要歸功於三拍子的圓舞曲,才能做到「欲蓋彌彰」。鍾興民老師在編曲中藏著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圓舞曲》,在優雅且隨時裙擺搖搖的音樂底下,自然可以為發音鬆綁,浪漫地走進廚房。
不過還是要問,這樣的諧音趣味為何會讓人樂此不疲?正巧近期這篇文章[註6]可以做為補充,作者分享原因來自我們從小都在學習如何「正確」書寫中文,諧音讓人們可以暫時逃出這種無形的控制。在日常語言使用上可以帶來荒謬感與愉悅感,比起需要正經地使用語言,鬆動結構、容納個人創意進駐並巧用文字,正是諧音梗會如此盛行的原因。
不過在李竺芯作品中的諧音還跨了語境,同音不同義的狀況比例會更多。這種情形有時會因為語言範疇過廣,而創作者並未察覺,在一部分群體中形成「內梗」。如:日文「空耳」直翻成中文,形成「一袋米扛幾樓」的梗圖笑話;日文「肌膚」(Hada)似是蒙藏民族的禮敬法器「哈達」,但來到布農族語境中卻近似「哈達斯」(表男性下體),鬧成笑話[註7]。這在〈Sakura Gansha〉充滿暗示的作品裡運用了非常多,如:「林のマンゴ」中的「マンゴ」(Mango)譯為「芒果」,但作品其實有意要指音近的「まんこ」(Manko,指女性私處);「ここ(這裡)」與「摳摳」(請自行意會)也同樣用了諧音雙關。
另外,李竺芯更將「諧音」運用到了音符中,在〈拄拄仔離開〉中,埋進了英文老派和聲常使用的「Doo-Wah Doo-Wah」,與歌詞中的「拄仔」相近,成為有趣的串接。
透過文字拉著音符,更拉著文化所形成的串聯,是《Suí 水》這張專輯最吸睛的地方,上可以透過女性書寫展示她的價值觀與文化傾向,下又能接觸普羅大眾,以輕鬆有趣的諧音方式引起共鳴。當中需要施展大量才華與用功是人們難以理解的,不過李竺芯並未把這些生硬、難解的問題拋給聽眾,而是透過音樂輕巧點出,偶而大膽嘗試人們的底線,這正向的驅動力便來自她賦予作品靈魂,而她或許也能開始認同創作中正流淌著她的血液,成為生命的延伸。
「拼湊」而來的文化,並非散亂,而是充滿生機
過去曾在百合花談三專《萬事美妙》的專訪[註8]中提到,美感永遠沒有對錯,只是不少人總認為台灣的美感要改善,覺得在橋下唱KTV的人很沒水準、大樓上加蓋鐵皮屋很醜…等,原因可能來自於,比起他國,台灣人更在乎「實用性」。過去島上經歷了許多外來人佔領、利用、搶奪物資,以至於人們生活艱苦,無暇顧及美感。但對不少本土創作者來說,這樣「無序」、「拼湊」而來的東西應該也是種美學,在百合花專輯中能體會,在李竺芯的專輯中似乎也能感受得到。也許《Suí 水》並不如概念專輯有著極為嚴謹的上下曲序關聯,但它展示了多元、吸納跨國文化特色的雜揉功力,讓我們知道它來自這片土地豢養,擁有極為強力的融合能力,最後自成一格。
如同台語中沒有「超人」這個字,但她卻寫了〈伍冬拾冬〉,用樸實的歌詞寫出一個個曾用生命澆灌台灣的「老飛俠」。
引用資料:
[註2] __ 妳的模樣 __《台灣查某囝》的封面背後2023.5-2023.9-李竺芯粉專貼文
[註3]觀察台灣早年兩性關係,可參考此篇,基本上同時期民初的女性作家都能窺得一二:《張愛玲早期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依附與出走的兩難困局》-王鳳儀(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註4]女性主義的性解放-何春蕤
[註7] 跨語言諧音:從星野源的〈肌Hada〉開始
[註8] 自由長出臺灣人的美感認同?專訪百合花Lilium 談三專《萬事美妙》,用音樂找出自己的「怪」與「美」-循聲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