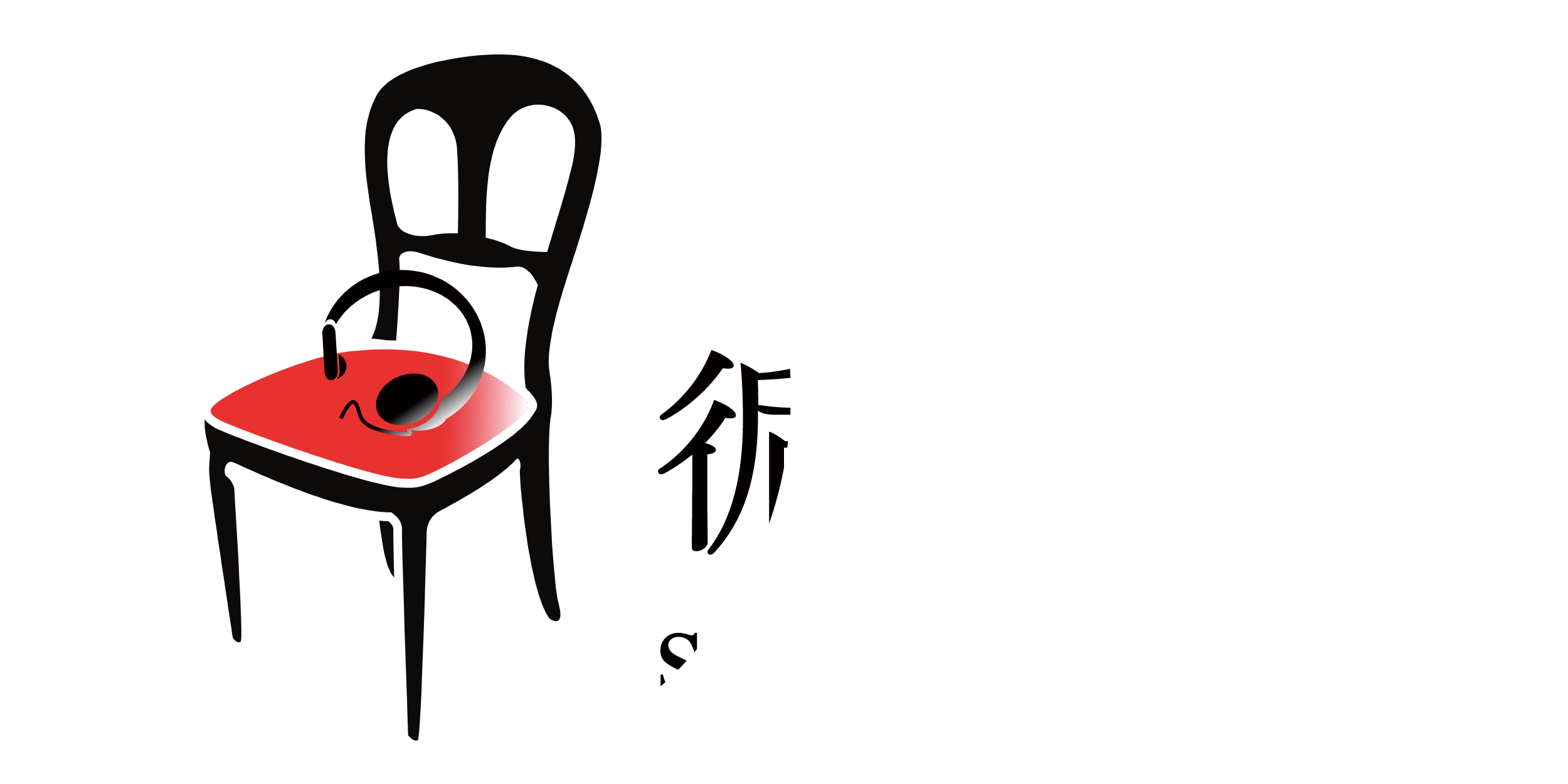嘟嘟和AJ變得更像暖男了。
還記得去年(2024)三月他們在《萬物皆玉》專場中段大寵粉,翻唱了New Jeans〈Super Shy〉。計謀得逞,將歌曲改成 JADE 風格後,兩人饒有興致地看著台下樂迷為他們準備的彩蛋驚喜尖叫。離男團僅差一步之遙,但最終他們還是收腳回到了搖滾,光這舉動就挺叛逆、挺搖滾的了。
不過筆者還是拋出了疑問:「過去聽了很多國外搖滾大團,有些都是好幾十年,會發現他們的表演或情緒宣洩方式始終如一,我猜想你們至少第一張專輯時應該很想像他們一樣吧?」
「我很嚮往那種生活,當時覺得一個搖滾樂團就是要憤怒地做完一張專輯,然後巡演過程喝酒、罵粉絲,最後再關起門來創作。」當時專訪已到中後段,嘟嘟分享從疫情以來到JADE第三張專輯《Creeper》發行時的心路。「但其實如果你今天很憤怒,頂多在Threads上發一篇文就夠了,不一定要把這個憤怒放在你的人生軌跡裡啊。」
「那種生活很酷沒錯,但我不一定要這麼做。」 嘟嘟說。
雙人搖滾樂團JADE自2019年發行首專《NEMO》到去年(2024)底第三張專輯《Creeper》登上串流,原先的搖滾銳氣在新專輯中褪去原先強烈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放入了不少相對耐聽與溫柔的作品,而歌詞更是在詞人葛大為的協助下得到深度拓展,少見地挖掘嘟嘟過去情感碎片,揉合成一張聽感至上,文字能竄入生活的搖滾專輯。
「欸?這兩個傢伙流行樂做得還蠻好的」
訪問一開始,和兩人聊到《Creeper》發行前讓人印象深刻的事,不約而同想到2023年和楊乃文合作的〈A Dream of Bonnie and Clyde〉。JADE和楊乃文兩組人搖滾品味相投、一見如故,不僅隔年(2024)一起在hito流行音樂獎上共演,也在楊乃文的《繆斯MUSE》演唱會台北最終場上驚喜擔任嘉賓。就連2024年初釋出的先行單曲〈萬物皆欲〉仍承接著他們標誌性聽感衝擊的前衛作風。
然而專輯釋出後,中段主打歌〈苦力怕〉一出卻頓感急轉彎,以降的〈清醒夢〉、〈漫走〉走往了方便將注意力放在歌詞的聆聽環境,細膩情感自然流淌而出。如此變化自然引起筆者好奇,拋出為何變得如此「暖」的疑惑。
「變暖嗎?我倒感覺比較像是自然轉變,做專輯到現在都是當下的心情抒發,不算有意為之。」嘟嘟說:「但如果硬要說的話,我希望這張專輯聽起來是比較沒有壓力的。」
似乎快進入核心,再來換了問法,從首專《NEMO》大肆放招、音樂繁複、才華盡出,二專《Snow White》開始施行減法,玩些音色帶來的情緒調度與營造一隅冷峻氛圍,再到現在。「你們會想在每一張專輯中做出特別的突破是嗎?」
嘟嘟思索了一下,「你這麼說好像有,但有點像是你講了之後,我回想它確實有突破,但當下沒有特別感覺。」他繼續說道:「不過我們在做每首歌時,心中一定會有想做些不一樣的設定,這些作品拼湊起來就會是一張完整的專輯,這樣就會讓人感覺我們有做很多突破。不過比起過去,我們希望在器樂表現、編曲邏輯上『變得相較簡單』。」
這是從第二張專輯時就已顯見的創作狀態,一路貫徹到現在這張《Creeper》似乎合理。這時AJ補充:「主要是第一張的反饋太明確(好),但不會是那種你開車或洗澡時會想放的那種歌。而第二張(專輯)因為疫情,大家整個心態都放緩了,我覺得創作還是會跟著我們人的狀態走。」
綻放地大笑
讓光亮渲染整座島
我會帶你看到
那些一瞬眼的美好-〈苦力怕〉
要說簡單,其實這次也調配了部分心力到歌詞。在專輯製作過程找來葛大為協助嘟嘟精雕文字。中段〈He’s coming〉接到〈苦力怕〉是一方完整的故事畫面,當中採草、搗土的聲音都來自他們共同喜愛玩的遊戲Minecraft(中譯:當個創世神),而「苦力怕」則是遊戲中的怪物名,將該怪物會用「自爆」方式攻擊玩家的特性,轉換成生活中可能出現的「恐怖情人」。悅耳的流行旋律搭配隱晦卻充滿「同歸於盡」激進言詞內容,雕塑出這首反差之作。
「不過趨於簡單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其實是個挑戰。」嘟嘟說:「因為長久以來就已經習慣編曲有種模式,一下子突然要由繁入簡,其實也是要經過很大的調整。」他回想過去至今,除了做JADE的作品外,偶而也會為他人作嫁,擔任編曲、製作人,建立流程是一件重要且能定位風格的職人心法,不過隨著嘟嘟這幾年心態漸變,精密的齒輪勢必得鬆開,再找到另一種組合方式繼續轉動。
他們就是這麼喜歡做有挑戰性的事。

「那我可以說這張專輯你們想讓它變得更耐聽,或者更流行、主流一點了?」筆者問。同樣,對於原先總被歸類為「獨立樂團」的JADE,這也是個相對有挑戰性的提問。
「可以啊!因為我也這麼覺得。」沒想到嘟嘟卻大方回應,「不過這都是創作當下的感覺,現在對於這種事情態度真的開放。」接著繼續補充:「但也不是說以後我們就要變成超『流行』的樂團。對我來說它只是一種嘗試,想知道我們做一張流行專輯會長什麼樣子。不過確實有歌迷寫說:『欸!這兩個傢伙流行樂做得還蠻好的!』」
「所以你們算嘗試得蠻成功的嘛!」筆者說。
「算成功。」嘟嘟說,「不過還是會看到一些網友罵你,但我是直接不看。」
「我是會看然後會心一笑的那種!」這時AJ突然搭話,「但就像你們吃東西看GOOGLE評論一定都會看差評對吧?我就會看對方是對哪邊不滿。『喔是這樣啊?SORRY囉!』」他模擬看到批評文時的態度,玩味地聳肩一笑。「我是一點都不會覺得被冒犯啦!只是對方剛好不喜歡而已。」
他們說,轉做流行做不好是最容易被罵的,但對作品始終保持信心的兩人,思索的卻從來不是流不流行。
「我覺得現在到了第三張專輯就是軟硬兼施,好像走到了一個平衡點。我想,這樣表演聽感就會很豐富,層次感應該很好。」AJ說,撒一點不同類型的音樂,未來在安排演唱會歌單上就能變化自如,他道出了對這張專輯的「功能性」用處。
嘟嘟則回到了每次改變都會被問的問題,「我知道有一種類型的聽眾他很怕你改變,他希望你永遠都長成他當初認識你的樣子。當你開始要做一點調整,就會說『你不像自己了』!但他不是我們啊?他沒有經歷過我們成長的背景,當然不會知道我們的心情改變。」這時他稍微緩下來,繼續說:「但我覺得這也挺自然的。當你了解之後會發現,其實他們也不是真的罵啊?就只是主觀的審美在作祟而已。」語氣之下,多少帶點無奈,當一個有個性的樂團多少有些不容易。
但你要說他們只是順著當下的感覺而在音樂上做出調整嗎?並不盡然。在慢下來的疫情當中他們思考了什麼?發生了什麼?促使JADE走向這條道路的原因肯定不會那麼簡單,於是筆者決定往更深處走去。
懂得下戲與成就對方之必要
「我發現你們這張專輯每一種樂器錄音地點幾乎都不一樣耶?」採訪當下,發現要往核心摸索,勢必得回到到創作的生活面。於是筆者突兀地詢問,因為正常樂團為了節省成本應該會在同一個地點分開錄音才對。
「其實我們從以前就這樣了。」嘟嘟回答,「我們算是個很喜歡分工的樂團,所以像吉他、貝斯都是完全交給我,這樣既有效率,也比較自在。不過也因為有這樣做音樂的觀念,才會讓我們稍微和其他團不一樣吧?」熱愛分工的他們,願意嘗試不同空間錄音,其實也是把空間對聲音的影響看得很重,「我一直沒有覺得一定得在某個模式下創作,在家也不會不能做音樂呀?只要你能做出想要的聲響,哪裡都可以做,在咖啡廳、坐飛機都可以。」
「其實我們會說那是『人味』。」AJ說。從第二張專輯以來,他們的音樂便開始保留了在科技進步下可以修掉的「不完美」聲音。
嘟嘟接著說:「有一派人會想要把它修掉,讓它完美。雖然我也是在某個層面上追求完美,但我比較是走『歪』的追求完美,我會想要儘可能在錄的時候,錄到我想要的take,後期剪貼能少做就少做。」他們說這種感覺很像在做LIVE演出,在聲音上保留了些許晃動感,甚至在vocal或木吉他錄音上留下實際收到的小雜音,那些「無傷大雅」的小瑕疵成就一位音樂創作者的個性一隅。
某部分來講,嘟嘟很願意在創作上展現他所有的真實,不過在透露生活上他則習慣點到為止。
認識嘟嘟的人會知道,他也是位老車控,喜歡手握方向盤的觸感、放久了會有點小裂痕的皮沙發,大概只有親近之人才有機會搭過他的車。於是把某段感情投射在這首歌當中,用些戲謔的唱腔回應已結束、思念起來卻有些蠢的關係。能透露的僅此而已,剩下請帶入各自的故事繼續發酵。
「其實從專輯第一首歌〈星球〉就能明白,你們會利用很大的空間去塑造一種無奈感,每首歌創作出來都不是要來解決事情,而是耽溺於某種過程,是嗎?」筆者問。
嘟嘟思索了片刻,給出了回應:「這些歌本來就是在挖掘過去的情緒,寫一個當時在困境中的角色。初衷只是還原過去某段時光眼睛看到或心理感受到的事,本來就沒有覺得要給他一個結局,或是告訴大家『我已經不是恐怖情人』、『我長大了』,沒有。」看著那些四散的記憶,遺憾已成定局、快樂當下也已充分體驗,現在的嘟嘟善於保留那個時空背景,在創作時成為某種情緒的催化劑。「這樣就好了。」他說。
不知為何,讓筆者想到嘟嘟曾在某則貼文中提到了「下戲」的重要性。
一天 一天 深陷 思緒凹陷
一點 一點 看穿 空洞的眼
彷彿置身 在絕對悲傷的輪迴
縱身 一躍 投入 上癮情結-〈沙發〉
「總覺得這樣創作會是一種比較能保護自己的方式,是這張專輯才開始的嗎?」筆者詢問。
「算是,也是因為這樣才意識到『身心靈健康』的重要性。」嘟嘟回答,語氣中帶有點事過境遷的釋然,「過去的我會很想把自己完全奉獻在音樂裡面,覺得這樣很酷、很帥,這樣才是真正的音樂人。所以在寫一些比較emo或是憤怒的歌時,整個創作過程我的情緒都會在裡面出不來。」他分享,尤其在做完《Snow White》準備要開始練團、跑宣傳,開始面對群眾時,才發現自己心態根本還沒準備好。「現在回頭來看,當時確實不太健康,後來才明白那是我自己入戲太深了。」
這時筆者趕緊問在一旁的AJ,他應該是那段過程接觸嘟嘟最長時間的人,「他過去會把某些憤怒跟你講或發洩在你身上嗎?」
沒想到嘟嘟搶著開口,「我記得在某年跨年夜整個人受不了,就打電話給他說:『出來陪我跨年!』那時精神快崩潰了,本來想自己出去走一走,後來發現不行,我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人群,然後就打給他。」
AJ頷首,接著說:「其實從創作就能明顯感覺到創作者本人的精神狀態,因為我都會聽到最原始的版本,這張(《Creeper》)的轉變很明顯。現在的作品聽起來舒舒服服的,帶著另一種成熟的自信,不是狂妄,而是拿出了現在最好的樣子。」
現在的樣子是成熟自信的表現,AJ看向嘟嘟,就像JADE這組樂團嘗試向內觀察了自己,在潰堤前驚險地止住,他們省去了劫後餘生的慶祝環節,取而代之的,是用音樂好好說故事。
想鬆也鬆不開的怪念頭
想好也好不起來的失落
想夢也夢不到 清醒的美夢
想追也追不上 那段舊時光-〈清醒夢〉
很少能在嘟嘟的作品中看到如此赤裸的告白,雖然在音樂表現上並不如其他首歌搶耳,卻是他專輯中特別想推薦的歌。
那麼AJ呢?平常擔任鼓手的他,似乎一直是成就嘟嘟作品畫面的人,在第二張專輯《Snow White》嘗試大部分皆由他作詞過後,第三張專輯有了什麼不同?於是我們先聊了〈Elephant〉。
「這首歌也是嘟嘟先丟過來的,我聽音樂會先有個畫面感,然後透過對它的第一印象去想有什麼故事。」AJ說,「我還是會有一個很明確的創作動機,像這首歌嘟嘟特別說主題要和大象有關,但我英文能力有限,聽起來有點隨興的躁,所以用稍微諷刺的方向來寫詞。」
以房間裡的大象為引,從索然無味的生活,心中想著要跳出框架卻還是留在原地,多麼諷刺。
接著我們又聊了〈漫走〉,AJ再次分享他如何好好服貼嘟嘟所建構的畫面,那些輕而短促的字句只希望相較有壓迫、密集感,與副歌做出落差。但對歌詞具體想說什麼仍未多提。
「之前在第二張專輯時也是這樣做嗎?」筆者忍不住詢問,畢竟是創作型樂團,難道沒有想說的話嗎?
「基本上都是這樣。」AJ說,「這算技術活嗎?如果嘟嘟腦中有個明確的樣子,我就會想辦法將他還原,再配合他的唱腔、唱歌的樣子,然後想他唱什麼詞比較好聽,怎樣符合他的形象…」有時嘟嘟一開始覺得唱不習慣的段落,AJ會堅持己見,讓他放一個晚上隔天再唱,反而就順了。
「你很了解他。」筆者說,這是肯定的。
「畢竟合作久了嘛!一定是有默契的。」AJ回。
「但你有想過作品從你自己開始發想嗎?」筆者問。
AJ沉思沒有很久,回答:「也會想啊!不管是歌詞或曲都會。但說實話我會覺得自己的『詞彙量』還不夠多,可能就只知道幾個和弦進行,所以要作曲的話我可能要花更多時間…不過老實說放假我其實更想躺著或打電動啦!」他和某一群音樂人其實也玩得很認真,於是大方地說:「結論只是懶而已啦!但我還是會想做。」
不過他還是提到目前創作比較以自己為主導的可行方法:「目前真算創作的話應該會這樣。比如現在主要都嘟嘟在寫曲,突然有一首歌很適合我腦中的畫面,我就會跟他提idea。」
「所以你比較像是心中有個酷點子都跟嘟嘟講,讓他產出東西給你去細編?這樣在創作會不會比較受到限制呢?」筆者追問。
「不會覺得被限制耶!我反而蠻期待這種的。」AJ回答得爽朗,繼續說:「記得我第一次嘗試寫的詞是〈City Boy〉(收錄於二專《Snow White》),寫完之後我發現蠻喜歡那種成就感的,畢竟他腦中的畫面一定還是會不一樣,但我寫出來由他唱出去,有時甚至超出我想像得好聽。」
其實到頭來只是筆者過度操心,希望兩人都能在自己的樂團中找到成就感,而對AJ來說「成就對方」就是收穫成就的主要來源。

「這大概就是和平常在外面做音樂工作的最大區別吧?一起產出東西跟在外面幹活的心情還是最不一樣的。」AJ說。
「這也是你們組團的其中一個原因嗎?」筆者問。
「一開始沒有,第一張專輯時我真就是個幹活仔,而且嘟嘟那時會編得很細,然後照著Demo寫的去做。」AJ回憶那段一路走來的歷程,繼續說:「那時候也剛認識他,我們還在到處幫別人做音樂,所以說實話我就是把錄音錄好、音樂做好。」
接著AJ繼續道出第二張專輯時的心路歷程,「我們到了第二張(專輯)疫情那段時間才真的比較熟,不然一開始其實我們只有表演、錄音時會到。到了第三張(專輯),我覺得現在狀態很不錯。」比起過去,現在嘟嘟會刻意留一大塊空間讓他的鼓能盡情發揮,「我聽了就知道他這個時候在臺上彈的話應該會想要看到我怎樣表現!」默契已從譜面上的交流,到只需一個舉動,就能明白對方的意思。
某種意義上,《Creeper》早已脫離了該不該持續突破的命題,而是幫助JADE重新定位了彼此在創作上不可或缺的位置,並找到舒適的方法繼續前進。
搖滾總要露出一點鋒芒吧?
與過去嚮往國外搖滾樂團敢衝、敢瘋的性格相比,最大的轉變還是要說回到疫情那段時間。「那時候大家都沒事啊!都開始在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很多人才真正把目光拉回到自己身上。」嘟嘟說,「我自己也是,那時候開始認識到自己確實有點崇洋媚外,最直接的現實是,小時候其實很愛聽五月天、周杰倫,可當我開始做樂團時,反而很抗拒。回頭看當時自己也蠻可愛的。」
於是放下那些銳利與言不由衷,換來嘟嘟那句「所以應該就是這句『長大了吧?』」
不過情緒趨於穩定還怎麼玩搖滾?
「確實。」嘟嘟也明白,但卻說:「 通常在這樣的情況下創作會很無聊,你生活就和正常人一樣,有什麼東西可以分享的?有些人就會去做社會觀察或是觀察其他人,當然這不是錯,但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偏無聊。」
於是他還是選擇回歸創作初衷,找到表達自己的方法,但以往寫出當下的作品已不再見效,最後他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去挖掘過去的自己。
「以前做完專輯總會有種被掏空的感覺,不過這次不會。」嘟嘟說。抓回了過去的情緒,想到十年前有點恐怖情人的自己、以前有過一段比較憂鬱的時期,用第三人稱的角度描寫自己,似乎不再那麼費力且上下戲自如。
回到《Creeper》專輯,最大框架大概就是空間與時間這不可測的維度範疇,〈星球〉落筆抒情,引出以「思念」為旨的專輯脈絡,在錯的時間遇見了像自己的人,最後收在以圖示意的〈ll l l l l TIME l l l l ll〉,依據愛因斯坦相對論,時間會隨速度愈接近光速而越慢,透過愈發急促的聲響,似乎渴望超越光速來實現回到過去的目的。然而事實是,縱使速度再快我們也回不到過去,所以這些思念留著就好,下戲之後日子繼續過。
「寫歌不外乎就是想找到同類嘛!有些人會自我投射到某首歌當中,我覺得只要這件事有發生,作品就已經圓滿了。」嘟嘟說,現階段的他認為作品一旦進入大眾視野,就不再屬於自己。「既然不屬於我,那也不用給他結局了。」
這和一般所認為的華語流行歌不同,大部分歌曲勢必得「暖收」,才能有某種教育意義。但嘟嘟卻不以為然,「硬要說我覺得某層面來講,自己真是個很喜歡搖滾樂的人,這就是我的叛逆。」他接著說:「我才沒有想要參照華語流行的公式去創作,但可以看見它們好的地方、美的地方,然後反映在我選用的音符、配器的處理上。而詞也有我自己的叛逆,不去迎合誰,或者會用流行曲式去創作其實很憤怒的作品。」
這就是搖滾,總要露出一點鋒芒吧!
「要不然我還真沒信心說自己是玩搖滾的,沒有這種精神存在,感覺我們可能真的會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男團。」兩人相視而笑,似乎知道樂迷可能不買單,但現階段請讓他們繼續當一會兒暖男吧?
用新作想辦法定義自己
《Creeper》釋出後收到不少反饋,好壞皆有,他們也早習以為常。不過嘟嘟卻說有一則回饋他難得地特別喜歡,寫著「JADE總是能在每一次新作品中一直在重新想辦法定義自己。」光這句話就知道對方懂,「因為他根本就不care你是不是變得油條或變流行了,他care的是 你是真正的音樂人,你必須要一直想辦法給自己新的定義。」

沒有人該承擔一輩子很酷的名號,他們也不願再用曾破碎的心去衝撞這個世界,偶而想唱點走心的歌,也拉回來分一些憤怒去創作一首歌,對JADE這組樂團來說,這樣的絕妙契合走到第三張專輯時,還真有種回甘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