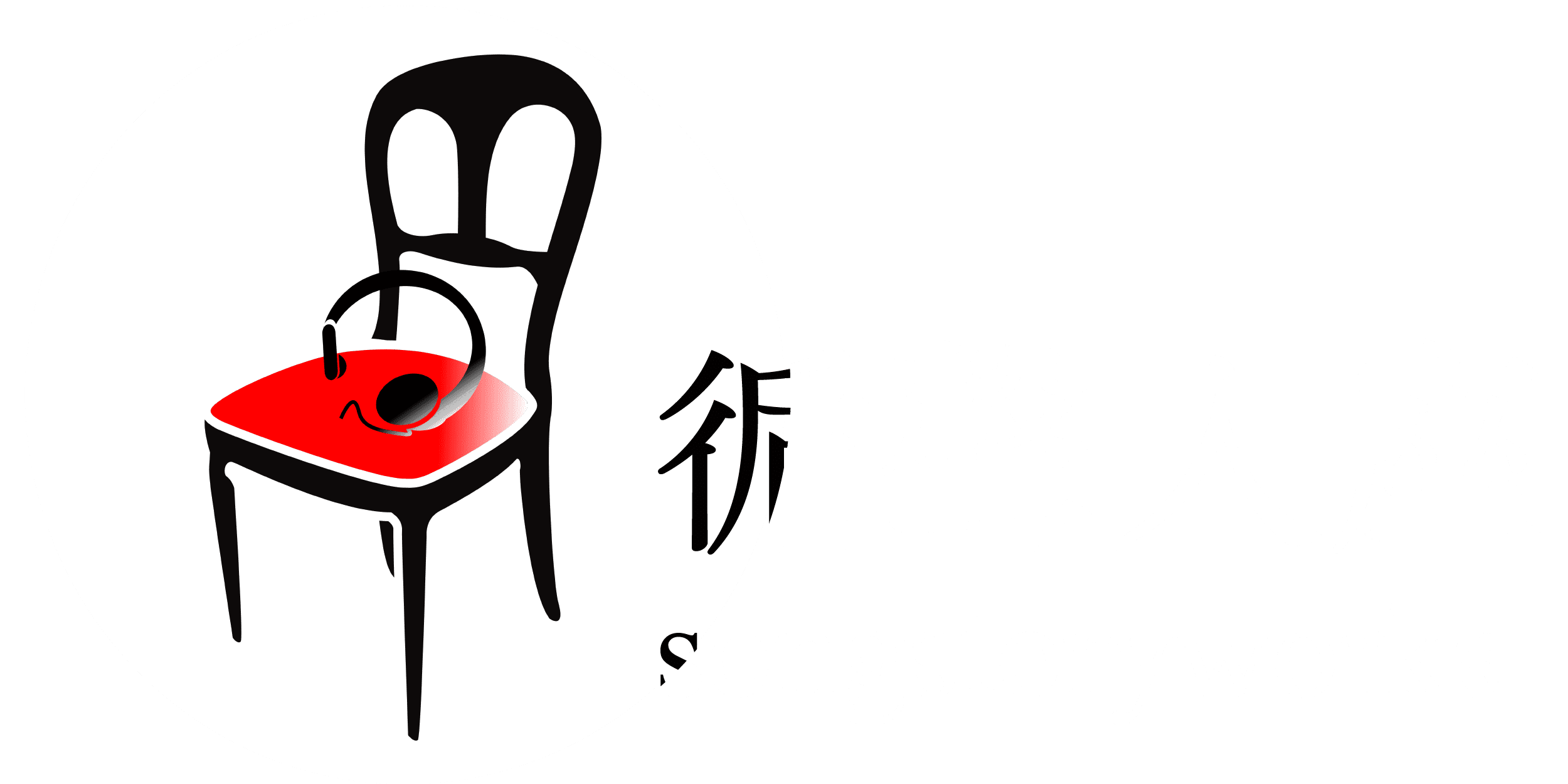1972年3月,一台無人太空飛行器在人類的見證下從地球出發,安然通過小行星帶、觀測了木星,飛越了海王星軌道,最後朝金牛座畢宿五的方向離開太陽系。在先鋒10號(Pioneer 10)飛行器當中,人們安裝了一塊刻有男女、地球位置等畫像的鍍金鋁板,試圖在未來某一天與截獲此板的外星生物取得溝通。其實不僅如此,過去人們也從地球向外太空發送電台、電視等訊號,就像被拋向大海的瓶中信,等待連結。
.
「一隻幼鳥孵化發出乞食聲開始,就不斷學習用不同的聲音表達自我。」
生命對溝通的渴望,一般來自身、心理需求,而人這複雜的生物,因為群居誕生語言,有了文字保存智慧,因為科技大幅減少溝通成本,更隨發展也往靈性和跨物種進行溝通。這些主發性的行為從心理層面來看,可能來自於人對孤獨的不適應,進而產生「溝通」的渴望。而《水逆》這張專輯會以「溝通」做為主題,除了源自鄭宜農小時候無法和奶奶好好溝通的遺憾,更是自《海王星》紀錄天真樂觀;《Pluto》從己身重新定義愛;《給天王星》從群體找尋自我後,最終透過「身分、情緒、語言、時間」,來重新整構自己。因為從自我為出發,探討溝通和其存在必要性,直至末端,才連結兩個延伸的專輯重點:「女性觀點」與「全台語作品」。
但對我來說,比起《給天王星》的群觀視角,其實《水逆》相當私人,縱然不比《Pluto》在自我中接觸到愛的自溺,卻因為自我與群體間保有游移的空間,在面對女性的標籤議題、台語的存亡之秋這樣顯學題目時,能如此巧妙地讓聽眾產生共感,進而串接,無非是這張專輯令人驚喜的地方。
故本篇將視野從大至小,連結鄭宜農從個性到觸及的議題,分別以專輯的宇宙觀、談自身對愛、情緒、溝通等感受,接著再談女性地位、台語文化等議題和技術面,讓《水逆》這張專輯能更加立體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海王.Pluto.天王:星象
「就像宇宙裡的星星,每一顆星星都註定孤獨,每一顆星星也都屬於同一個宇宙。」
在天上發光明的星星,有的燃燒自己照耀他星,少數塌陷成黑洞,將周圍的光一線不留地圈裹,而那些各具特色的行星,有些則靠著巨量氣體壓縮而瑩瑩發光,但絕大部分則領著恆星給予的光和熱,在夜空掛著特殊的顏色。不管光源從何而來,我們抬頭仰望看見的發光體,都成了星象,被記錄在各種演算法之中。
前三張專輯都以星球命名的鄭宜農,用每顆行星帶給她的溫柔,來詮釋每個階段的自己,如上一張專輯《給天王星》,用傾斜的地軸形成天差地別的黑夜與白天,來暗示此階段的她已擁有獨立姿態、特立於眾生。而這次《水逆》也以水星為代表,在星象上產生「與溝通有關」的連結。
而我想,宜農會將這四張專輯框架放在星體上,除了對星象的興趣外,很大部分和她對人保持一定「距離」卻不離人群的個性有關。這樣的距離感,其實在她專輯收尾歌中能體會到,如《Pluto》中的〈酒店關門之後〉聽似療癒紓壓,但背後卻「為什麼傷感 難道是驚覺所有的話說出來都是徒然」;《給天王星》的〈千千萬萬〉:「千千萬萬句說不出口的話 在黑夜裡放光明」隔著距離展示分別的光明,以及《水逆》中〈無人看見的所在〉縮小大愛,「甘願做無路用的我」,只因為她知道「其實足濟代誌我攏無確定」。才發現,再大的世界,最多只容得下另一人的進駐,而大部分需要面對的孤獨,都填滿在星星發光之外的地方。
溝通.關係.遺憾
掃視鄭宜農過去的經歷,曾有過被無端拋到人群面前公然、私下斷臆的時候,在與當時前夫坦承、與父親很快達成和解之後,才開始練習和自己溝通。
面對最熟識卻也陌生的自己,必須統一陣線面對他人嘴裡竄出的惡意時,她選擇在一聲聲似是碎片的雨聲、熱水燒開的鳴聲堆疊下,展開一場極其平穩卻慍怒的抗爭,收在〈天已經要光〉當中。
這首歌的鋪成從主觀視角開展到客觀的群體感受,「光」是一種出生即覆滅的存在,導引人意識到現實和內心世界的震動,被重擊的心聲穩定而撼動地輸出,搜尋著來自四面八方的惡意源頭。鄭宜農向我們展示內心還未平衡,外頭卻把語言當成殺人工具般地不斷放矢,「對話猶未出世就已經歸天」自始自終從未達成和解。是溝通之中,最讓人遺憾無解的時刻。
《水逆》在文本及創作風格上趨向內斂,就連如此憤怒的作品,都還把「惡意從你的喙內開花」形容地文雅而淡漠,甚至連對腦中繁雜敦促它停止時,都以〈Duludilida〉這首歌輕快地唱著”So are you gonna shut up”。不管是和自己的溝通,或透過溝通建立起的關係橋梁,甚而走至關係結束,誕生而來的遺憾,似乎都經過如此工巧的方式熨燙過,實現了專輯統一的調性,聲音低至〈天已經要光〉,而最高則是〈親愛的〉這首唱來需要相當技巧的歌。
「心愛的 若是予你看見我的目屎 你敢會感受著 你並毋是孤單一個」
如果〈天已經要光〉代表即將毀天覆地的場景,〈親愛的〉則站在了光譜另一端,展現言語中最柔情的一面。在分享自身內心脆弱的同時,達到與他人的共感,這必定是情緒通過整理後,才得以直進對方情感核心的證明。
如今,鄭宜農也有過站上大舞台被人仰視的時刻,她總能在自身的作品裡,投射出外表交流中難以感受到的真實情感。而會令她擁有目前的自適,想必是因面對困難時總能直面而上的積極個性吧?才會在「水逆」之下談起最不擅長的溝通,並以身體力行的方式,用她最不擅長的語言鋪排成專輯,並雕琢著每一首歌。
失根.尋根
這世代其實包容性很高,卻也容易因遺忘而忽視掉重要的議題。2019年4月,鄭宜農站上總統府前舞台,背後打上象徵同婚意志的彩虹光雕,唱著「你相信我吧!就像我相信你一樣」的歌詞,儼然成為台灣獨立女聲和性平運動的代言人。
「這張專輯的脈絡、每一個元素,其實都是圍繞著『身為一個這樣的女性的觀點』,或者『身為一個這樣的女性會遇到的事』。」
我聽見過去宜農唱著〈玉仔的心〉時,為著台灣早期代工業旺盛的辛苦女工發聲。她以玉潔的心,代表著縱使外表被遮蔭,「淹沒在茫茫的城市」,但願望仍在,抱持著初心待價而沽。
而專輯中〈新世紀的女兒〉,也包裹著電子,偏實驗性的碎拍音樂,搭配MV從學生、上班族、熟女、結婚四個身分,穿插表情從雀躍到猶疑。表達女性總是嚴重地被貼上標籤,縱使現在的社會開放,但也往往很難與自己或家人達成和解。而放觀到不只女性的議題上,也同時針砭「多元性別」,為整個社會所有人都會遇到的問題傳遞這項重要訊息-「捀著妳的選擇 一切攏無簡單」。
連上了女性,甚至多元性別的根,鄭宜農也為過去被迫害、視為禁忌、低俗的語言發聲。雖然在前幾張專輯中多少會出現台語歌,聽起來並不陌生,但要全然踏足台語領域,勢必在用字是否精準、詞曲結合是否造成倒音、氣口是否有特色等面向多加琢磨。
可暫且撇除技術不談,也不以「傳承」之詞曉以大義,筆者認為使用台語其實是青壯年時期的創作者,用來記錄與上一代長輩的連結及自我童年的重要橋梁。比如在〈做風颱〉中加入了祖孫間的溫情對話,並哼著日語童謠〈桃太郎〉片段,將童年時遇到颱風天停電,僅有一盞燭光卻是全家人都在的安心情景收入期中。而筆者特別喜歡鄭宜農以「詩人將看見的風景紀錄在書裡」的意象,將「語言保存」變成一件浪漫唯美的事情,落筆以〈或許就變成書裡的風景〉為題,收錄台語、原住民語言間的對答,儼然成為一方風景。
於是語言的根,就這麼被溫柔地捧接,不那麼刻板枯燥地傳承了下來。
犧牲.延展
「使用任何一種文化,包括台語,以及他背後所承載的歷史,甚至是不同地域性的腔調等,心裡都想著這些東西是很珍貴的,我要很小心、很尊敬的對待…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我覺得重要性在於讓人變得謙卑。」
筆者相信,語言使用終究會走向簡便易理解一路,但卻不該斷送語言本身具韻味十足的魅力,像是在華語中埋藏隱喻,台語則用俚語包藏深意,雖然在歌詞創作中,以俚語帶入顯得彆扭,卻不容忽視在日常應用上的扼要。而在我看來,《水逆》之所以被稱為不為新而新的新台語作品,除了工於台語用字,還可能做了這兩點,試圖和其他語言做交割,讓它流向更為舒適,容易讓人接受的語境上做呈現。
.
第一、語言轉換,使它在作品裡更具流動性
在鄭宜農的《水逆》當中,似乎可以看見以下規律:台語善用於敘事、英語用做點綴、華語則拿來提綱挈領。不管過去從散文、詩詞角度來看,都注重韻律性,在加入音樂、節奏後,更需要語言展現出流動感,句末間的押韻是基本功,更進階的還得是在符合台語語境上又展現詞曲咬合。舉《水逆》被認為用字精巧原因之一押韻精準,以〈Duludilida〉為例:
結果咱踅甲戇戇 踅甲戇戇(gōng)
踅袂出暗崁的衝動(tāng)
心內底每日相挵(lòng)
將外在漫無目的,內心卻衝突無比的情感浮上了檯面,才會想用shut up來打破這可怕的循環。
另外,展現語言轉換最具流動感的,當屬〈天已經要光〉中最後一句「留我一个人慢慢埋(tâi) 慢慢Die」用近音將掩埋和死亡連成一串行雲流水的動作。
.
第二、拉前了台語發聲部位,與其他語言融成一線
相對於立足於台語歌壇的有名歌手,他們各個在台語的氣口上多有特色,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台語的發聲部位相較於華語來得後面,以同年入金曲的曹雅雯《禁》專輯為例,當中唯一一首華語歌〈城市三花貓〉便能聽出發聲落差。但鄭宜農的台語歌其實多是在輕快中盡顯特色,並穿插其他語言的快語,毫無違和地融成一線,這同樣在曹雅雯〈All you can fly〉中唱著”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只是在《水逆》當中除了在〈Duludilida〉唱著”So are you gonna shut up, please?”外,還有做為背景音唱著” Fight darlin flight darlin fight”,但整體發聲卻提前的〈新世紀的女兒〉。
透過模糊發聲部位,與其他語言交融,讓作品具有延展度,也是讓聽眾耳朵得到更多刺激的關鍵。
在訊號脫節之前,別讓那些未講出來的話成為遺憾
先前發射到太空的先鋒10號,NASA於2006年做了最後一次聯絡嘗試,最終沒了回應,逕直地走向了下一個星系。「水逆」其實一直在發生吧?日常生活中我們有權利選擇何種方式與親近之人溝通,但卻鮮少在對頻上進行交流,於是把遺憾交給了那些過去未主動調頻,如今卻已失聯的人。因此,把握和自己、重要他人對話的空間,成了疫情之後更顯重要的議題。
《水逆》這張專輯該放在2022年當中哪一個位置呢?我們都知道「溝通」的必要性,但在疫情即將結束的時期,我們少了許多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多了與自己的對話,同時我們也乘載了許多來不及說的遺憾,卻也意識到真情的重要性。這張作品,不但對宜農本人來說是相當躍進的挑戰,也為社會提出實質性的討論話題,實在不可多得。
參考文章